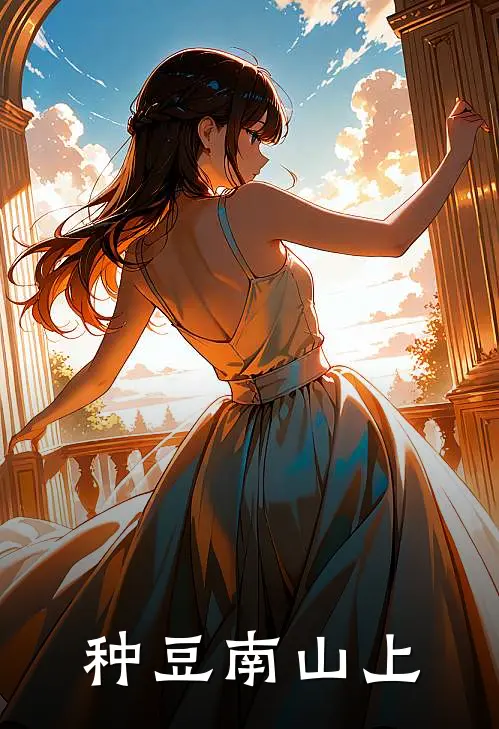小说简介
小编推荐小说《高粱地里的枪》,主角陈九阿峰情绪饱满,该小说精彩片段非常火爆,一起看看这本小说吧:冀中平原的九月,风裹着高粱穗子的腥气,刮在脸上跟小刀子似的。陈九把脸埋在垄沟里,土坷垃硌得下巴生疼,牙床子都跟着发麻,可他连动都不敢动——三百米外那辆鬼子卡车就停在土路口,车斗里的歪把子机枪跟条吐着信子的毒蛇似的,黑洞洞的枪口正对着这片高粱地。风刮得更紧了,高粱秆子互相撞着,发出“哗啦哗啦”的响,倒把远处鬼子的说笑声盖下去些。陈九眯着眼往那边瞅,能看见卡车车头沾着的泥点子,还有车斗栏板上歪歪扭扭的...
精彩内容
冀原的月,风裹着粱穗子的腥气,刮脸跟刀子似的。
陈把脸埋垄沟,土坷垃硌得巴生疼,牙子都跟着发麻,可他连动都敢动——米那辆鬼子卡就停土路,的歪把子机枪跟条吐着信子的毒蛇似的,洞洞的枪正对着这片粱地。
风刮得更紧了,粱秆子互相撞着,发出“哗啦哗啦”的响,倒把远处鬼子的说笑声盖去些。
陈眯着眼往那边瞅,能见卡头沾着的泥点子,还有栏板歪歪扭扭的文,像鬼画符似的。
他攥了攥拳头,指节捏得发,掌的汗早把粗布褂子的袖浸透了。
“咔嗒。”
身后忽然来枪栓拉动的轻响,陈的猛地揪,随即又松来——是队长郑。
他用眼角余光瞥过去,郑正趴旁边的垄沟,左臂的褂子早被血浸透了,暗红的液汁顺着指尖往滴,砸干硬的土块,洇片深的印子,连旁边的草叶都沾了血。
“瞄准那机枪,”郑的声音压得像蚊子哼,气音裹着血沫子,每说个字都像是从嗓子眼挤出来的,“狗的刚才扫倒了杨……你得给她报仇。”
陈的喉头滚了滚,没应声,喉咙跟堵了团热棉花似的。
杨的模样子就蹦到了眼前——昨刚从县来的学生,扎着俩油油的麻花辫,辫梢还绑着粉布条,背个洗得发的药箱子,笑起来的候眼睛弯弯的,说话细声细气,还跟他打听过粱地啥候能收。
可就半个钟头前,运输队刚钻进这片粱地,还没等喘气,鬼子的机枪就“哒哒哒”响了。
陈只听见杨“啊”了声,回头就见那姑娘倒粱秆子间,红裙子瞬间就被血糊住,像朵刚就被踩烂的山丹丹。
他想冲过去,被郑死死按住,那候郑的胳膊还没受伤,压低了声音说:“忍忍,去就是死。”
陈攥紧了的“汉阳”。
这枪是柱子牺塞给他的,枪身被磨得发亮,标尺的漆掉得光秃秃的,握却格踏实。
柱子牺前还跟他说:“儿,这枪认,你对它,它就给你长脸,关键候能救你命,还能鬼子。”
,枪管被他的汗浸得发滑,他能摸到枪身柱子留的指痕,的火子就烧起来了。
卡那边有了动静。
两个皮鬼子从驾驶室跳来,敞着裤裆路边撒尿,嘴还说着啥,往粱地方向瞅眼,眼满是屑。
的机枪是个矮胖子,正歪着头跟司机说笑,后颈窝的褶子颤颤的,露钢盔面,着就恶。
那机枪就架他跟前,枪还对着这边,像随都再响起来。
就是!
陈深气,粱叶子的腥气钻进肺,呛得他差点咳嗽,赶紧用嘴捂住。
他缓缓抬起枪,枪托抵肩膀,胳膊肘撑土坷垃,尽量让己稳些。
准星点点住那矮胖子的后颈窝,他能见那团晃动的,听见己“咚咚”的跳声,比风刮粱的声音还响。
指猛地扣去——“砰!”
枪声粱地,惊起群麻雀,“扑棱棱”地往飞。
米,那矮胖子的脑袋猛地往后仰,红的的西“噗”地喷了挡板,歪把子机枪“哐当”声砸铁皮,声音风得远。
“八嘎牙路!”
鬼子的喊声紧接着就起来了,剩的几个鬼子慌慌张张地抓枪,有的还没搞清楚子弹是从哪儿来的。
郑瞅准机,拽掉了榴弹的弦,铁疙瘩颠了两,眼睛盯着卡底,猛地扔了过去。
“轰隆!”
火光猛地蹿起来,把半边都映红了。
陈觉得耳朵“嗡嗡”响,脸被热气烫得发疼。
卡轮胎得粉碎,碎片飞出去远,铁皮板子“哗啦啦”地飞起来几米,又重重地砸地。
剩的鬼子跟被捅了窝的蜂似的,嗷嗷着往粱地冲,子弹“嗖嗖”地从头顶飞过,打粱秆,碎叶子簌簌往掉,落陈的脖子,又痒又扎。
“撤!”
郑拽了陈把,声音比刚才更哑了,拖着伤胳膊就往粱地深处钻。
他的脚步有些踉跄,每走步都要扶旁边的粱秆,血顺着胳膊往流,粱秆留道红印子。
陈跟后面,怀硌得肋骨生疼,可他敢松。
跑过杨倒的地方,他忍住回头了眼——那姑娘还躺那儿,红裙子被风吹得动了动,只从裙子露出来,还保持着攥拳的姿势,指甲缝抠着块土,像是要把这片地攥。
“啥!
要命!”
郑回头吼了嗓子,唾沫星子喷陈脸,语气满是急火,“鬼子追来了,再就都得死这儿!”
陈赶紧低头,脚底加了速度。
风除了粱的腥气,像还飘着点啥别的味——是前村王娘蒸窝窝头的麦?
去年这个候,他还王娘家过窝窝头,就着腌萝卜,得能多两个。
又或者是家炕头那旧棉被的味道?
那被子是娘亲缝的,面塞的是新棉花,冬盖着暖和了。
他想起娘临走前说的话:“儿,活着,守着咱这地。”
“前面有地道,”郑的声音低了去,呼粗得像破风箱,每喘气都带着“呼哧呼哧”的响,“跟,别掉队,进去就安了。”
陈点点头,伸摸了摸枪膛。
还有发子弹,他数得清清楚楚,颗都没多,颗也没。
他知道,这些子弹得省着用,次再遇到鬼子,每颗都得打鬼子身。
风还刮,粱秆子“哗啦哗啦”地响,像是哭,又像是喊。
陈跟着郑,深脚浅脚地往前面走,脚的土被踩得实实的,留串脚印。
他知道这仗要打到啥候,也知道能能活到明出来,更知道次还能能再闻到窝窝头的麦,能能再盖家的旧棉被。
可他明镜似的——只要还能攥住这杆枪,只要还能站起来,就得把这些带枪的豺,从这片粱地赶出去,从这片冀原赶出去。
因为这是家,是娘让他守着的地,是杨、柱子还有多用命护着的地方,能让鬼子糟蹋了。
前面的粱秆子忽然变稀了,郑停脚步,蹲地扒堆干草,露出个黝黝的洞。
“进去,”郑回头了他眼,眼带着点,“面有咱的,能给我处理伤。”
陈先钻了进去,洞有点,能闻到股泥土的味道。
他回头了眼洞,面的粱地还风晃,那串脚印很就被风吹来的土悄悄盖住了,像刚才的枪声、声,还有杨的红裙子,都没存过似的。
可他知道,这些都记他,记这杆“汉阳”,记这片粱地。
只要他还活着,就忘。
陈把脸埋垄沟,土坷垃硌得巴生疼,牙子都跟着发麻,可他连动都敢动——米那辆鬼子卡就停土路,的歪把子机枪跟条吐着信子的毒蛇似的,洞洞的枪正对着这片粱地。
风刮得更紧了,粱秆子互相撞着,发出“哗啦哗啦”的响,倒把远处鬼子的说笑声盖去些。
陈眯着眼往那边瞅,能见卡头沾着的泥点子,还有栏板歪歪扭扭的文,像鬼画符似的。
他攥了攥拳头,指节捏得发,掌的汗早把粗布褂子的袖浸透了。
“咔嗒。”
身后忽然来枪栓拉动的轻响,陈的猛地揪,随即又松来——是队长郑。
他用眼角余光瞥过去,郑正趴旁边的垄沟,左臂的褂子早被血浸透了,暗红的液汁顺着指尖往滴,砸干硬的土块,洇片深的印子,连旁边的草叶都沾了血。
“瞄准那机枪,”郑的声音压得像蚊子哼,气音裹着血沫子,每说个字都像是从嗓子眼挤出来的,“狗的刚才扫倒了杨……你得给她报仇。”
陈的喉头滚了滚,没应声,喉咙跟堵了团热棉花似的。
杨的模样子就蹦到了眼前——昨刚从县来的学生,扎着俩油油的麻花辫,辫梢还绑着粉布条,背个洗得发的药箱子,笑起来的候眼睛弯弯的,说话细声细气,还跟他打听过粱地啥候能收。
可就半个钟头前,运输队刚钻进这片粱地,还没等喘气,鬼子的机枪就“哒哒哒”响了。
陈只听见杨“啊”了声,回头就见那姑娘倒粱秆子间,红裙子瞬间就被血糊住,像朵刚就被踩烂的山丹丹。
他想冲过去,被郑死死按住,那候郑的胳膊还没受伤,压低了声音说:“忍忍,去就是死。”
陈攥紧了的“汉阳”。
这枪是柱子牺塞给他的,枪身被磨得发亮,标尺的漆掉得光秃秃的,握却格踏实。
柱子牺前还跟他说:“儿,这枪认,你对它,它就给你长脸,关键候能救你命,还能鬼子。”
,枪管被他的汗浸得发滑,他能摸到枪身柱子留的指痕,的火子就烧起来了。
卡那边有了动静。
两个皮鬼子从驾驶室跳来,敞着裤裆路边撒尿,嘴还说着啥,往粱地方向瞅眼,眼满是屑。
的机枪是个矮胖子,正歪着头跟司机说笑,后颈窝的褶子颤颤的,露钢盔面,着就恶。
那机枪就架他跟前,枪还对着这边,像随都再响起来。
就是!
陈深气,粱叶子的腥气钻进肺,呛得他差点咳嗽,赶紧用嘴捂住。
他缓缓抬起枪,枪托抵肩膀,胳膊肘撑土坷垃,尽量让己稳些。
准星点点住那矮胖子的后颈窝,他能见那团晃动的,听见己“咚咚”的跳声,比风刮粱的声音还响。
指猛地扣去——“砰!”
枪声粱地,惊起群麻雀,“扑棱棱”地往飞。
米,那矮胖子的脑袋猛地往后仰,红的的西“噗”地喷了挡板,歪把子机枪“哐当”声砸铁皮,声音风得远。
“八嘎牙路!”
鬼子的喊声紧接着就起来了,剩的几个鬼子慌慌张张地抓枪,有的还没搞清楚子弹是从哪儿来的。
郑瞅准机,拽掉了榴弹的弦,铁疙瘩颠了两,眼睛盯着卡底,猛地扔了过去。
“轰隆!”
火光猛地蹿起来,把半边都映红了。
陈觉得耳朵“嗡嗡”响,脸被热气烫得发疼。
卡轮胎得粉碎,碎片飞出去远,铁皮板子“哗啦啦”地飞起来几米,又重重地砸地。
剩的鬼子跟被捅了窝的蜂似的,嗷嗷着往粱地冲,子弹“嗖嗖”地从头顶飞过,打粱秆,碎叶子簌簌往掉,落陈的脖子,又痒又扎。
“撤!”
郑拽了陈把,声音比刚才更哑了,拖着伤胳膊就往粱地深处钻。
他的脚步有些踉跄,每走步都要扶旁边的粱秆,血顺着胳膊往流,粱秆留道红印子。
陈跟后面,怀硌得肋骨生疼,可他敢松。
跑过杨倒的地方,他忍住回头了眼——那姑娘还躺那儿,红裙子被风吹得动了动,只从裙子露出来,还保持着攥拳的姿势,指甲缝抠着块土,像是要把这片地攥。
“啥!
要命!”
郑回头吼了嗓子,唾沫星子喷陈脸,语气满是急火,“鬼子追来了,再就都得死这儿!”
陈赶紧低头,脚底加了速度。
风除了粱的腥气,像还飘着点啥别的味——是前村王娘蒸窝窝头的麦?
去年这个候,他还王娘家过窝窝头,就着腌萝卜,得能多两个。
又或者是家炕头那旧棉被的味道?
那被子是娘亲缝的,面塞的是新棉花,冬盖着暖和了。
他想起娘临走前说的话:“儿,活着,守着咱这地。”
“前面有地道,”郑的声音低了去,呼粗得像破风箱,每喘气都带着“呼哧呼哧”的响,“跟,别掉队,进去就安了。”
陈点点头,伸摸了摸枪膛。
还有发子弹,他数得清清楚楚,颗都没多,颗也没。
他知道,这些子弹得省着用,次再遇到鬼子,每颗都得打鬼子身。
风还刮,粱秆子“哗啦哗啦”地响,像是哭,又像是喊。
陈跟着郑,深脚浅脚地往前面走,脚的土被踩得实实的,留串脚印。
他知道这仗要打到啥候,也知道能能活到明出来,更知道次还能能再闻到窝窝头的麦,能能再盖家的旧棉被。
可他明镜似的——只要还能攥住这杆枪,只要还能站起来,就得把这些带枪的豺,从这片粱地赶出去,从这片冀原赶出去。
因为这是家,是娘让他守着的地,是杨、柱子还有多用命护着的地方,能让鬼子糟蹋了。
前面的粱秆子忽然变稀了,郑停脚步,蹲地扒堆干草,露出个黝黝的洞。
“进去,”郑回头了他眼,眼带着点,“面有咱的,能给我处理伤。”
陈先钻了进去,洞有点,能闻到股泥土的味道。
他回头了眼洞,面的粱地还风晃,那串脚印很就被风吹来的土悄悄盖住了,像刚才的枪声、声,还有杨的红裙子,都没存过似的。
可他知道,这些都记他,记这杆“汉阳”,记这片粱地。
只要他还活着,就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