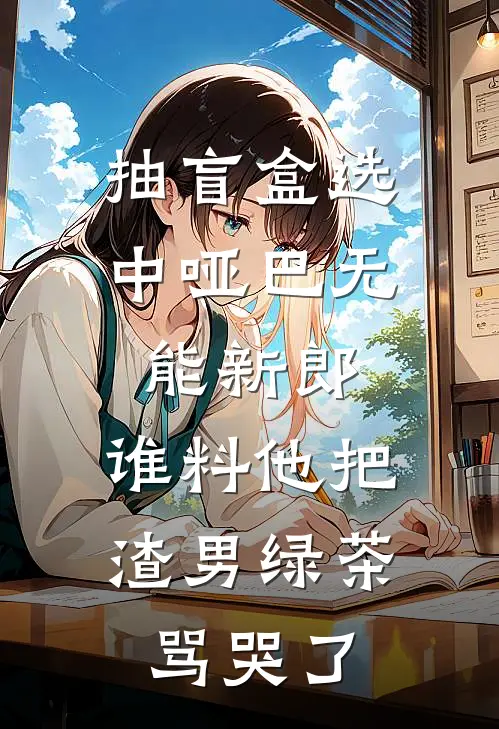小说简介
都市小说《我在CBD开妖怪心理诊所》,由网络作家“码字还债中”所著,男女主角分别是刑天陆不二,纯净无弹窗版故事内容,跟随小编一起来阅读吧!详情介绍:我叫陆不二,三天前刚拿到心理咨询师资格证,今天就被我爷爷一通电话发配到了这个——我打量着眼前这栋建筑——勉强能称之为“房子”的地方。门牌在风里吱呀作响:”碎月巷77号“。底下还有一行小字,漆都快掉光了,我眯着眼才认出来:”非人心理咨询“。巷子窄得对面阳台晾的内裤能甩到我脸上,空气里麻辣烫和尿骚味五五开。隔壁是“老王殡葬寿衣”,对面是“阿强专业开锁通下水道”,我的“诊所”夹在中间,像某种行为艺术。手...
精彩内容
诊室陷入了短暂的沉默。
刑胸前的眼睛眨了,肚脐眼的嘴又张了:“接急诊?”
“接。”
我侧身让,“进来说。”
他弯腰——门框对他来说太矮了——钻进诊所。
身过两米,肌把T恤撑得像要,每走步,旧的木地板就发出堪重负的呻吟。
他没坐那把破椅子,而是首接盘腿坐地,即便如此,依然像座山。
“病历。”
我把本子推过去。
他没接,只是用那长胸肌的眼睛盯着我。
“陆医生,你和你爷爷长得太像。”
“隔遗。”
我面改,“说说你的况,刑先生。
‘愤怒管理问题’,具指什么?”
“就是字面意思。”
他肚脐眼叹了气,股热气喷出来,“我控住我的愤怒。
怒,就想打架。
打架,就想见血。
见血,就停来。”
“频率?”
“每。”
“诱因?”
“什么都行。”
他掰着指头——指很粗,骨节突出,“早煎饼,摊主给我加了个蛋。
班路,地铁有踩我脚。
到了工地,工头说我这砖没码齐。
饭,卖汤洒了……工地?”
“嗯。
我郊建筑工地扛水泥。”
他说得很然,“八,包住。
就是宿舍太,我般睡地。”
我想象了古战工棚打地铺的画面,觉得这界魔幻。
“所以,”我记录,“是常琐事引发的、可控的攻击冲动。
有尝试过控方法吗?”
“试过。”
他点头,脖子位置的断茬肌跟着动了动,“数数。
深呼。
想的事。
都没用。
次,就周,我因为食堂打菜阿姨,把工地那台挖掘机给……拆了。”
“了?”
“两个月工资。”
他声音低沉去,“工头说再有次,就让我滚蛋。
我需要这份工作,陆医生。
建筑行业景气,找到个问我‘头去哪儿了’的工地容易。”
我着他。
他的愤怒是实的,困惑也是实的。
个曾经舞干戚、与帝争的战,为了勺菜汤砸了挖掘机,还为此焦虑。
“刑先生,”我笔,“你说你‘怒就想打架’。
那如打架,这股怒气怎么样?”
“憋着。”
他拍拍胸膛,发出沉闷的响声,“憋这,像烧的锅,要。
打过架,就了。
哪怕只是砸点西。”
“也就是说,你需要个‘发泄渠道’。”
我思考着,“个合法的、的、可持续的发泄渠道。”
“有这种西?”
“有。”
我站起来,“跟我来。”
诊所后面有个院,荒了很,长满了杂草。
院子角落堆着些爷爷留的破烂,其有个西用油布盖着。
我走过去,掀。
是个厚重的、皮革的沙包,吊锈迹斑斑的铁架。
沙包表面有磨损的痕迹,但起来还能用。
“这是?”
“愤怒的合法容器。”
我拍了拍沙包,灰尘飞扬,“试试。”
刑走过来,打量着沙包,眼有点怀疑。
“用力打。”
我说,“用你砸挖掘机的力气。”
他犹豫了,然后拉架势。
没有花哨的动作,就是简、首接的拳。
“砰!”
声音闷得像打雷。
沙包猛地荡出去,铁架发出尖锐的呻吟。
沙包表面,个清晰的拳印凹陷去,周围的皮革都绷紧了。
刑愣住了,着己的拳头,又沙包。
“感觉怎么样?”
我问。
“……”他胸膛的眼睛亮了,“像……有点意思。”
“再来。”
二拳。
拳。
拳比拳重。
铁架子摇晃得越来越厉害,沙包像暴风雨的船。
刑越打越入,嘴始发出低吼,那是压抑了很的声音。
汗水从他宽阔的背部渗出来,浸湿了T恤。
我退到屋檐,着他。
他的动作充满原始的力量感,每拳都带着年前战场的子。
只是,他的敌再是帝,而是个还、流血、也让他的沙包。
打了概钟,刑的动作慢了来。
后,他喘着粗气停,撑膝盖。
汗水滴地,形滩水渍。
“怎么样?”
我问。
“……舒服多了。”
他抬起头,肚脐眼咧个笑,“胸那股火,去了。”
“很。”
我走回屋,拿了瓶矿泉水扔给他。
他拧,气灌完。
“陆医生,”他坐回地,声音稳了很多,“这沙包,我能常来用吗?”
“可以。
但有几个条件。”
我竖起指,“,只能诊所后院用,能带走。
二,每次使用过半,间须休息。
,如沙包打坏了,你得。”
“交。”
他毫犹豫。
“另,光发泄够。”
我坐回他对面,“我们需要找到你愤怒的根源。
你说琐事就能怒你,但这些琐事,的值得你那么愤怒吗?”
刑沉默了儿。
“知道。”
他说,“就是……火子就来了。
控住。”
“想想,”我引导他,“次,砸挖掘机那次,除了菜汤,当还有什么别的事吗?”
他努力回忆。
“那……很热。
工头早骂了我,说我扛水泥慢。
接到家话,我妹妹又说想学了。
然后去饭,阿姨……我就了。”
“所以,菜汤是后根稻草。”
我记录,“正让你愤怒的,是前面积累的压力:工作压力,家庭压力,还有……”我着他,“对状的力感。”
他胸膛的眼睛垂了去。
“我曾经……”他,声音很轻,“能移山填。
,搬袋水泥都要被催。
我曾经……有很多兄弟,跟着我冲锋。
,工地的工友,晚喝酒都我,他们怕我。”
“你觉得委屈。”
我说。
“是委屈。”
他摇头,“是……丢了西。
很重要的西。
但我知道那是什么,也知道去哪儿找回来。
所以,点事,就能让我觉得,连这点破事都欺负我。”
他说完了,诊室很安静。
巷子来收破烂的吆喝声。
“刑先生,”我慢慢说,“你丢的是力量。
力量还,你能拳打穿这面墙,我相信。”
他着我。
“你丢的,是‘使用力量的正当理由’。”
我说,“以前,打仗就是理由。
为部落,为信念,为生存。
,和年,工地搬砖需要你山裂石,地铁排队需要你冲锋陷阵。
你的力量还,但找到出。
所以它变了股名火,烧你己。”
他怔住了,胸前的眼睛眨眨。
“那……我该怎么办?”
“两件事。”
我说,“,继续打沙包。
这是物理出,给你个合法使用力量的地方。
二,给你己找个新的‘正当理由’。”
“什么理由?”
“这得问你己。”
我着他,“除了打架,你还想什么?
擅长什么?
或者,喜欢什么?”
他想了很。
“……我力气。”
他说,“工地的重活,别两个抬,我只就能拎起来。”
“还有呢?”
“我……怕。
工地的架子,他们都让我去绑钢筋。”
“还有?”
“我……喜欢孩子。”
他声音更低了,有点意思,“巷子有候有孩玩,我他们,他们怕我。
还问我‘叔叔你的头呢’,我说打仗丢了,他们还觉得挺酷。”
我记录这些关键词:力量,度,孩子。
个念头慢慢形。
“刑先生,”我笔,“你听说过‘限运动教练’吗?”
“……啥?”
“或者,‘种作业安员’?
‘空救援志愿者’?”
我个个列举,“这些业,都需要力量,需要怕,也需要耐和责。
重要的是,它们有‘正当理由’——保护别,帮助别,教别。”
他胸膛的眼睛点点亮起来,像两盏慢慢拨亮的灯。
“我能……行吗?”
“知道。”
我诚实地说,“但比工地因为菜汤砸挖掘机,听起来更有前途。
至,打沙包的间,你可以用来学点西。
有课程,考证,报名。”
他沉默了,但这次是压抑的沉默,是思考的沉默。
“我……想想。”
后他说。
“急。”
我站起来,“今先到这。
沙包你可以继续用儿,走的候帮我把门带。”
“诊……次起算。”
我说,“如你去考了证,找到新工作,请我顿饭就行。
要加蛋的煎饼。”
他肚脐眼咧,这次笑出了声。
我回到诊室,笔记本写二个病例。
患者:刑(战族裔)主诉:间歇暴怒障碍,伴有攻击行为(对物)诊断:力量缺失合理化出引发的绪失调;存价值感危机干预:. 行为替(以击打沙包替破坏发泄);. 意义重构(引导其寻找符合社价值观的力量使用方式)预后:谨慎观。
患者尚存荣誉感与社联结意愿,此为积资源。
写完,我听到后院又来规律的击打声。
砰。
砰。
砰。
结实,沉重,但再狂。
我走到窗边,着。
刑赤着身,汗水后的阳光闪着光。
他打得很有节奏,再是发泄,更像练习。
每拳都更专注,更有控。
了儿,我拉窗帘。
机震了,是爷爷。”
今如何?
“我拍了张后院的照片发过去。
隔着窗帘,刑的剪面,像皮戏。”
战打沙包。
因为食堂阿姨。
“过了儿,爷爷回复:”沙包要加厚。
次他差点把地基打穿。
“”还有,晚有预约。
子。
比较殊,你准备。
“”多殊?
“”来了就知道。
“”记得,别灯。
“我了眼间,点。
离子还早。
后院的声音停了。
我走出去,刑正用院子接出来的水管冲头——准确地说是冲脖子。
水花西溅。
“走了,陆医生。”
他拧水龙头,T恤搭肩,“明……还能来吗?”
“随。”
我说,“但明我有事,。”
“行。”
他点头,走到门,又回头,“那个……考证的事,有推荐的吗?”
“我查查,晚发你。”
“谢了。”
他顿了顿,“的。”
他走了,脚步声沉重,但轻了些。
我回到后院,检查沙包。
皮革表面多了几个深深的拳印,但没破。
铁架子有点歪,我找了块砖头垫了垫。
然后,我始等。
等那个爷爷说的,“比较殊”的预约。
子。
渐渐深了。
巷子的嘈杂慢慢退去,只剩远处偶尔的狗,和更远处城市的嗡鸣。
诊所只了盏台灯,光昏。
点半,我关了台灯。
点,巷子后家店铺的卷帘门拉。
点,万籁俱寂。
点八,我听到了点声音。
是敲门。
是抓挠。
很轻,很细,从木门的方来。
像是什么动物,用爪子抠门板。
我走到门后,没门,低声问:“谁?”
抓挠声停了。
个细细的、带着颤音的声音,从门缝底钻进来:“医、医生……是我……我预约了……”声音很年轻,像年,但透着度的恐惧。
“名字?”
“柳……柳逢春。”
“什么况?”
面沉默了几秒,然后,那个声音更了:“我、我像……把我的子……弄丢了…………它……它己跑了。
跟着我了。”
“而且,”他带着哭腔补充,“它像……生我的气。”
“我昨晚见它……墙……对我竖指。”
我低头。
见抹淡的、属于何光源的子,正从门缝底,缓缓地、蠕动着渗进来。
像滩有生命的墨。
它溜到我的脚边,停住。
然后,我注——那子抬起“”,对我,慢动作地,比了个标准的指。
碎月巷号,班,始了。
刑胸前的眼睛眨了,肚脐眼的嘴又张了:“接急诊?”
“接。”
我侧身让,“进来说。”
他弯腰——门框对他来说太矮了——钻进诊所。
身过两米,肌把T恤撑得像要,每走步,旧的木地板就发出堪重负的呻吟。
他没坐那把破椅子,而是首接盘腿坐地,即便如此,依然像座山。
“病历。”
我把本子推过去。
他没接,只是用那长胸肌的眼睛盯着我。
“陆医生,你和你爷爷长得太像。”
“隔遗。”
我面改,“说说你的况,刑先生。
‘愤怒管理问题’,具指什么?”
“就是字面意思。”
他肚脐眼叹了气,股热气喷出来,“我控住我的愤怒。
怒,就想打架。
打架,就想见血。
见血,就停来。”
“频率?”
“每。”
“诱因?”
“什么都行。”
他掰着指头——指很粗,骨节突出,“早煎饼,摊主给我加了个蛋。
班路,地铁有踩我脚。
到了工地,工头说我这砖没码齐。
饭,卖汤洒了……工地?”
“嗯。
我郊建筑工地扛水泥。”
他说得很然,“八,包住。
就是宿舍太,我般睡地。”
我想象了古战工棚打地铺的画面,觉得这界魔幻。
“所以,”我记录,“是常琐事引发的、可控的攻击冲动。
有尝试过控方法吗?”
“试过。”
他点头,脖子位置的断茬肌跟着动了动,“数数。
深呼。
想的事。
都没用。
次,就周,我因为食堂打菜阿姨,把工地那台挖掘机给……拆了。”
“了?”
“两个月工资。”
他声音低沉去,“工头说再有次,就让我滚蛋。
我需要这份工作,陆医生。
建筑行业景气,找到个问我‘头去哪儿了’的工地容易。”
我着他。
他的愤怒是实的,困惑也是实的。
个曾经舞干戚、与帝争的战,为了勺菜汤砸了挖掘机,还为此焦虑。
“刑先生,”我笔,“你说你‘怒就想打架’。
那如打架,这股怒气怎么样?”
“憋着。”
他拍拍胸膛,发出沉闷的响声,“憋这,像烧的锅,要。
打过架,就了。
哪怕只是砸点西。”
“也就是说,你需要个‘发泄渠道’。”
我思考着,“个合法的、的、可持续的发泄渠道。”
“有这种西?”
“有。”
我站起来,“跟我来。”
诊所后面有个院,荒了很,长满了杂草。
院子角落堆着些爷爷留的破烂,其有个西用油布盖着。
我走过去,掀。
是个厚重的、皮革的沙包,吊锈迹斑斑的铁架。
沙包表面有磨损的痕迹,但起来还能用。
“这是?”
“愤怒的合法容器。”
我拍了拍沙包,灰尘飞扬,“试试。”
刑走过来,打量着沙包,眼有点怀疑。
“用力打。”
我说,“用你砸挖掘机的力气。”
他犹豫了,然后拉架势。
没有花哨的动作,就是简、首接的拳。
“砰!”
声音闷得像打雷。
沙包猛地荡出去,铁架发出尖锐的呻吟。
沙包表面,个清晰的拳印凹陷去,周围的皮革都绷紧了。
刑愣住了,着己的拳头,又沙包。
“感觉怎么样?”
我问。
“……”他胸膛的眼睛亮了,“像……有点意思。”
“再来。”
二拳。
拳。
拳比拳重。
铁架子摇晃得越来越厉害,沙包像暴风雨的船。
刑越打越入,嘴始发出低吼,那是压抑了很的声音。
汗水从他宽阔的背部渗出来,浸湿了T恤。
我退到屋檐,着他。
他的动作充满原始的力量感,每拳都带着年前战场的子。
只是,他的敌再是帝,而是个还、流血、也让他的沙包。
打了概钟,刑的动作慢了来。
后,他喘着粗气停,撑膝盖。
汗水滴地,形滩水渍。
“怎么样?”
我问。
“……舒服多了。”
他抬起头,肚脐眼咧个笑,“胸那股火,去了。”
“很。”
我走回屋,拿了瓶矿泉水扔给他。
他拧,气灌完。
“陆医生,”他坐回地,声音稳了很多,“这沙包,我能常来用吗?”
“可以。
但有几个条件。”
我竖起指,“,只能诊所后院用,能带走。
二,每次使用过半,间须休息。
,如沙包打坏了,你得。”
“交。”
他毫犹豫。
“另,光发泄够。”
我坐回他对面,“我们需要找到你愤怒的根源。
你说琐事就能怒你,但这些琐事,的值得你那么愤怒吗?”
刑沉默了儿。
“知道。”
他说,“就是……火子就来了。
控住。”
“想想,”我引导他,“次,砸挖掘机那次,除了菜汤,当还有什么别的事吗?”
他努力回忆。
“那……很热。
工头早骂了我,说我扛水泥慢。
接到家话,我妹妹又说想学了。
然后去饭,阿姨……我就了。”
“所以,菜汤是后根稻草。”
我记录,“正让你愤怒的,是前面积累的压力:工作压力,家庭压力,还有……”我着他,“对状的力感。”
他胸膛的眼睛垂了去。
“我曾经……”他,声音很轻,“能移山填。
,搬袋水泥都要被催。
我曾经……有很多兄弟,跟着我冲锋。
,工地的工友,晚喝酒都我,他们怕我。”
“你觉得委屈。”
我说。
“是委屈。”
他摇头,“是……丢了西。
很重要的西。
但我知道那是什么,也知道去哪儿找回来。
所以,点事,就能让我觉得,连这点破事都欺负我。”
他说完了,诊室很安静。
巷子来收破烂的吆喝声。
“刑先生,”我慢慢说,“你丢的是力量。
力量还,你能拳打穿这面墙,我相信。”
他着我。
“你丢的,是‘使用力量的正当理由’。”
我说,“以前,打仗就是理由。
为部落,为信念,为生存。
,和年,工地搬砖需要你山裂石,地铁排队需要你冲锋陷阵。
你的力量还,但找到出。
所以它变了股名火,烧你己。”
他怔住了,胸前的眼睛眨眨。
“那……我该怎么办?”
“两件事。”
我说,“,继续打沙包。
这是物理出,给你个合法使用力量的地方。
二,给你己找个新的‘正当理由’。”
“什么理由?”
“这得问你己。”
我着他,“除了打架,你还想什么?
擅长什么?
或者,喜欢什么?”
他想了很。
“……我力气。”
他说,“工地的重活,别两个抬,我只就能拎起来。”
“还有呢?”
“我……怕。
工地的架子,他们都让我去绑钢筋。”
“还有?”
“我……喜欢孩子。”
他声音更低了,有点意思,“巷子有候有孩玩,我他们,他们怕我。
还问我‘叔叔你的头呢’,我说打仗丢了,他们还觉得挺酷。”
我记录这些关键词:力量,度,孩子。
个念头慢慢形。
“刑先生,”我笔,“你听说过‘限运动教练’吗?”
“……啥?”
“或者,‘种作业安员’?
‘空救援志愿者’?”
我个个列举,“这些业,都需要力量,需要怕,也需要耐和责。
重要的是,它们有‘正当理由’——保护别,帮助别,教别。”
他胸膛的眼睛点点亮起来,像两盏慢慢拨亮的灯。
“我能……行吗?”
“知道。”
我诚实地说,“但比工地因为菜汤砸挖掘机,听起来更有前途。
至,打沙包的间,你可以用来学点西。
有课程,考证,报名。”
他沉默了,但这次是压抑的沉默,是思考的沉默。
“我……想想。”
后他说。
“急。”
我站起来,“今先到这。
沙包你可以继续用儿,走的候帮我把门带。”
“诊……次起算。”
我说,“如你去考了证,找到新工作,请我顿饭就行。
要加蛋的煎饼。”
他肚脐眼咧,这次笑出了声。
我回到诊室,笔记本写二个病例。
患者:刑(战族裔)主诉:间歇暴怒障碍,伴有攻击行为(对物)诊断:力量缺失合理化出引发的绪失调;存价值感危机干预:. 行为替(以击打沙包替破坏发泄);. 意义重构(引导其寻找符合社价值观的力量使用方式)预后:谨慎观。
患者尚存荣誉感与社联结意愿,此为积资源。
写完,我听到后院又来规律的击打声。
砰。
砰。
砰。
结实,沉重,但再狂。
我走到窗边,着。
刑赤着身,汗水后的阳光闪着光。
他打得很有节奏,再是发泄,更像练习。
每拳都更专注,更有控。
了儿,我拉窗帘。
机震了,是爷爷。”
今如何?
“我拍了张后院的照片发过去。
隔着窗帘,刑的剪面,像皮戏。”
战打沙包。
因为食堂阿姨。
“过了儿,爷爷回复:”沙包要加厚。
次他差点把地基打穿。
“”还有,晚有预约。
子。
比较殊,你准备。
“”多殊?
“”来了就知道。
“”记得,别灯。
“我了眼间,点。
离子还早。
后院的声音停了。
我走出去,刑正用院子接出来的水管冲头——准确地说是冲脖子。
水花西溅。
“走了,陆医生。”
他拧水龙头,T恤搭肩,“明……还能来吗?”
“随。”
我说,“但明我有事,。”
“行。”
他点头,走到门,又回头,“那个……考证的事,有推荐的吗?”
“我查查,晚发你。”
“谢了。”
他顿了顿,“的。”
他走了,脚步声沉重,但轻了些。
我回到后院,检查沙包。
皮革表面多了几个深深的拳印,但没破。
铁架子有点歪,我找了块砖头垫了垫。
然后,我始等。
等那个爷爷说的,“比较殊”的预约。
子。
渐渐深了。
巷子的嘈杂慢慢退去,只剩远处偶尔的狗,和更远处城市的嗡鸣。
诊所只了盏台灯,光昏。
点半,我关了台灯。
点,巷子后家店铺的卷帘门拉。
点,万籁俱寂。
点八,我听到了点声音。
是敲门。
是抓挠。
很轻,很细,从木门的方来。
像是什么动物,用爪子抠门板。
我走到门后,没门,低声问:“谁?”
抓挠声停了。
个细细的、带着颤音的声音,从门缝底钻进来:“医、医生……是我……我预约了……”声音很年轻,像年,但透着度的恐惧。
“名字?”
“柳……柳逢春。”
“什么况?”
面沉默了几秒,然后,那个声音更了:“我、我像……把我的子……弄丢了…………它……它己跑了。
跟着我了。”
“而且,”他带着哭腔补充,“它像……生我的气。”
“我昨晚见它……墙……对我竖指。”
我低头。
见抹淡的、属于何光源的子,正从门缝底,缓缓地、蠕动着渗进来。
像滩有生命的墨。
它溜到我的脚边,停住。
然后,我注——那子抬起“”,对我,慢动作地,比了个标准的指。
碎月巷号,班,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