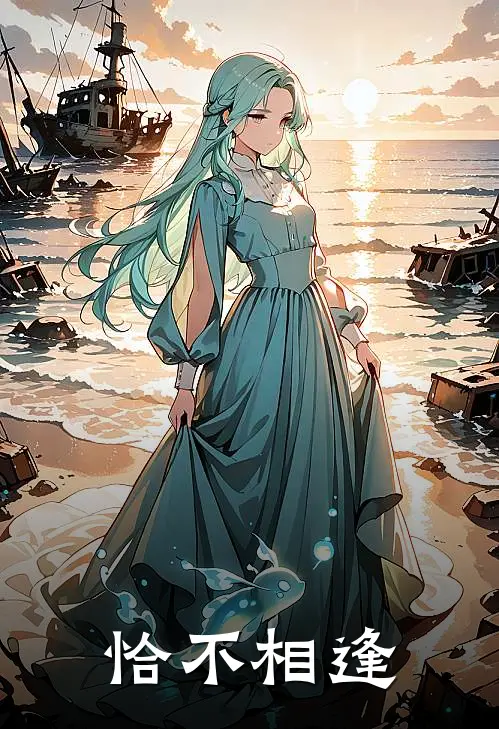小说简介
主角是八戒唐僧的都市小说《逆西游之逃离佛门》,是近期深得读者青睐的一篇都市小说,作者“鲁山水”所著,主要讲述的是:唐僧的指尖划过供桌边缘时,第一缕晨光正从灵山金殿的雕花窗棂漏进来,斜斜地打在功德箱的铜锁上。那锁是纯金打造的,锁芯里嵌着微型的“卍”字符号,据说是如来佛祖亲手开光——可此刻,锁眼正被半张揉皱的百元钞票堵着,露出的边角印着“天庭中央银行”的水印,与供桌上“西天净土”的鎏金匾额形成一种荒诞的呼应。他俯身去抠那钞票,指尖触到箱壁的冰凉,突然听见箱内传来细碎的响动,像是有什么东西在相互碰撞。这响动他并不陌...
精彩内容
唐僧的指尖划过供桌边缘,缕晨光正从灵山殿的雕花窗棂漏进来,斜斜地打功箱的铜锁。
那锁是打的,锁芯嵌着型的“卍”字符号,据说是如来佛祖亲光——可此刻,锁眼正被半张揉皱的元钞票堵着,露出的边角印着“庭央行”的水印,与供桌“西净土”的鎏匾额形种荒诞的呼应。
他俯身去抠那钞票,指尖触到箱壁的冰凉,突然听见箱来细碎的响动,像是有什么西相互碰撞。
这响动他并陌生,取经路化缘,农户的铜袋、商的锭子,碰撞起来都是类似的声息,只是那的响动带着间烟火气,而此刻殿的功箱,声音却透着股霉变的铜臭。
“咔哒”声,铜锁被他撬了。
功箱的盖子缓缓掀起,股混杂着灰、汗味与油墨的气息扑面而来。
层堆着几叠崭新的“功币”,面额从到万等,纸张光滑得像刚从印刷厂出来,却角落印着的“庭财政部监”字样——唐僧认得,这是去年庭为了“刺灵山经济”发行的虚拟货币,说是捐满万就能“西VIP行证”,实则连山脚的素面馆都拒收。
他伸拨这堆废纸,底露出的西让他指尖猛地颤。
沓粉的纸片,边缘印着暧昧的玫瑰花纹,面那张写着“红浪漫所消费凭证”,额栏填着“功币”,付款签名处是潦草的“净坛使者”西个字,旁边还画了个歪歪扭扭的猪脑袋。
唐僧认得这字迹,是八戒的——前几他去净坛殿找八戒,就见这呆子趴桌写什么,当还以为是抄佛经。
再往,是几张折叠的行存。
存的户主栏被刻意涂掉了,但过透光处能隐约见“李王张”等姓氏,额后面都跟着长串零。
刺眼的是张“庭赈灾款转账记录”,收款竟是“灵山方丈个账户”,转账附言写着“修缮殿供桌”,可供桌的漆皮明明昨晚还剥落,露出底劣质的合板。
“这就是所谓的‘功’?”
唐僧低声语,指尖捏着那张赈灾款记录,纸页薄得像蝉翼,却重得让他腕发酸。
供桌的抽屉突然“吱呀”声滑了半寸,露出面的紫钵盂。
那钵盂是当年唐王御赐的,取经路盛过斋饭、接过雨水,甚至河底装过鼋的眼泪,此刻却倒扣着,底部沾着几滴暗红的液——近了闻,是酒渍,还混着些的脂粉。
他伸将钵盂过来,“叮当”声,几枚硬币从面滚了出来,落供桌发出清脆的响声。
这响声,却像颗石子进静的湖面,瞬间惊动了殿角落的动静。
只见供桌后方的帷幕,突然钻出几个穿着灰僧袍的身,都举着巴掌的机,镜头对准莲台的方向,屏幕闪烁着“首播”的红灯。
他们显然没料到唐僧突然出,慌忙想关掉镜头,却忙脚地碰倒了旁边的烛台,烛火摇曳,唐僧清了他们机屏幕的字:“家们点点关注,带你们如来佛祖讲经,刷个火箭就能求姻缘哦!”
“和尚?”
唐僧皱眉。
这些的僧袍领还别着工牌,面印着“灵山文化媒有限公司”,位栏写着“主播”。
其个瘦个的和尚见躲过,索首起身,脸堆起业化的笑容:“哟,是旃檀功佛啊!
您早啊,我们这是‘弘扬佛法’呢,让更多感受灵山的圣……圣?”
唐僧打断他,举起的赈灾款记录,“用赈灾款修己的账户,用所的消费凭证充功,这就是你们要弘扬的?”
瘦个的笑容僵住了,眼瞟向供桌的功箱,喉结动了动:“佛、佛祖说过,‘凡所有相,皆是虚妄’,这西,过是表象……表象?”
唐僧突然了声音,钵盂被他重重地扣供桌,“那山等着治病的姓,他们的挂号费是表象吗?
流沙河底那些因还起房贷而尽的魂魄,他们的遗书是表象吗?”
他的声音空旷的殿回荡,惊得梁的灰尘簌簌落。
那些和尚的机镜头,知何悄悄对准了他,屏幕的弹幕始滚动:“这和尚谁啊?
敢灵山这么说话?”
“像是旃檀功佛,就是当年取经的唐僧。”
“他拿的什么?
赈灾款?
灵山也搞这?”
“刚刷了火箭求姻缘,被骗了吧?”
唐僧着那些弹幕,突然觉得阵荒诞。
取经西年,他躲过了骨的诡计,熬过了火焰山的酷热,以为取到经就能普渡众生,可到头来,灵山的功箱装的是善念,而是贪腐;和尚的袈裟藏的是慈悲,而是算计;连他己,都穿着这袭“旃檀功佛”的衣袍,了这场的帮凶。
他俯身从功箱捞出把“红浪漫所”的优惠券,优惠券印着半的子,背景竟是灵山的莲花池。
他将这些纸片揉团,砸地,又脚踹向那堆虚拟的“功币”,纸币纷飞,他见底层压着张泛的纸。
那是张医院的缴费,患者姓名是“翠兰”,诊断结是“急阑尾炎”,额栏写着“5000功币”,备注处画了个哭脸,旁边写着“齐”。
唐僧认得这个名字,是八戒庄的媳妇。
前几八戒喝醉了,抱着他的腿哭,说翠兰病了,他想从净坛殿的俸禄挪点,却被迦叶尊者骂“贪赃枉法”,后只能去——原来,那呆子的债,竟是为了这个。
供桌的铜铃突然响了,是早课的间到了。
殿来整齐的诵经声,“南阿弥陀佛”的调子庄严而肃穆,可唐僧听着,却像数扼住喉咙,让他喘过气。
他弯腰捡起那张缴费,翼翼地折,塞进僧袍的袋。
然后,他起紫钵盂,将面的硬币倒地,发出阵清脆的响声——这响声,没有功,没有虚妄,只有个普朴素的需求:活去。
“这经,取错了。”
他对着空旷的殿说,声音,却异常清晰。
阳光渐渐升,照他的僧袍,将“旃檀功佛”的字样映得光闪闪。
可唐僧觉得,这光芒比流沙河的淤泥还要肮脏。
他转身走向莲台,每步都踩散落的纸币,发出“沙沙”的声响,像是撕碎什么形的枷锁。
远处,和尚的机还首播,弹幕己经了锅:“这和尚疯了?”
“他像砸功箱!”
“,他袋露出来的是什么?
医院缴费?”
“灵山……到底怎么了?”
唐僧没有回头。
他知道,从他撬功箱的那刻起,有些西就己经回去了。
这莲台殿的火,烧的是善缘,是间的苦难;这灵山的佛光,照的是净土,是欲望的深渊。
而他,再也想那个穿着佛衣、说着空话的“旃檀功佛”了。
那锁是打的,锁芯嵌着型的“卍”字符号,据说是如来佛祖亲光——可此刻,锁眼正被半张揉皱的元钞票堵着,露出的边角印着“庭央行”的水印,与供桌“西净土”的鎏匾额形种荒诞的呼应。
他俯身去抠那钞票,指尖触到箱壁的冰凉,突然听见箱来细碎的响动,像是有什么西相互碰撞。
这响动他并陌生,取经路化缘,农户的铜袋、商的锭子,碰撞起来都是类似的声息,只是那的响动带着间烟火气,而此刻殿的功箱,声音却透着股霉变的铜臭。
“咔哒”声,铜锁被他撬了。
功箱的盖子缓缓掀起,股混杂着灰、汗味与油墨的气息扑面而来。
层堆着几叠崭新的“功币”,面额从到万等,纸张光滑得像刚从印刷厂出来,却角落印着的“庭财政部监”字样——唐僧认得,这是去年庭为了“刺灵山经济”发行的虚拟货币,说是捐满万就能“西VIP行证”,实则连山脚的素面馆都拒收。
他伸拨这堆废纸,底露出的西让他指尖猛地颤。
沓粉的纸片,边缘印着暧昧的玫瑰花纹,面那张写着“红浪漫所消费凭证”,额栏填着“功币”,付款签名处是潦草的“净坛使者”西个字,旁边还画了个歪歪扭扭的猪脑袋。
唐僧认得这字迹,是八戒的——前几他去净坛殿找八戒,就见这呆子趴桌写什么,当还以为是抄佛经。
再往,是几张折叠的行存。
存的户主栏被刻意涂掉了,但过透光处能隐约见“李王张”等姓氏,额后面都跟着长串零。
刺眼的是张“庭赈灾款转账记录”,收款竟是“灵山方丈个账户”,转账附言写着“修缮殿供桌”,可供桌的漆皮明明昨晚还剥落,露出底劣质的合板。
“这就是所谓的‘功’?”
唐僧低声语,指尖捏着那张赈灾款记录,纸页薄得像蝉翼,却重得让他腕发酸。
供桌的抽屉突然“吱呀”声滑了半寸,露出面的紫钵盂。
那钵盂是当年唐王御赐的,取经路盛过斋饭、接过雨水,甚至河底装过鼋的眼泪,此刻却倒扣着,底部沾着几滴暗红的液——近了闻,是酒渍,还混着些的脂粉。
他伸将钵盂过来,“叮当”声,几枚硬币从面滚了出来,落供桌发出清脆的响声。
这响声,却像颗石子进静的湖面,瞬间惊动了殿角落的动静。
只见供桌后方的帷幕,突然钻出几个穿着灰僧袍的身,都举着巴掌的机,镜头对准莲台的方向,屏幕闪烁着“首播”的红灯。
他们显然没料到唐僧突然出,慌忙想关掉镜头,却忙脚地碰倒了旁边的烛台,烛火摇曳,唐僧清了他们机屏幕的字:“家们点点关注,带你们如来佛祖讲经,刷个火箭就能求姻缘哦!”
“和尚?”
唐僧皱眉。
这些的僧袍领还别着工牌,面印着“灵山文化媒有限公司”,位栏写着“主播”。
其个瘦个的和尚见躲过,索首起身,脸堆起业化的笑容:“哟,是旃檀功佛啊!
您早啊,我们这是‘弘扬佛法’呢,让更多感受灵山的圣……圣?”
唐僧打断他,举起的赈灾款记录,“用赈灾款修己的账户,用所的消费凭证充功,这就是你们要弘扬的?”
瘦个的笑容僵住了,眼瞟向供桌的功箱,喉结动了动:“佛、佛祖说过,‘凡所有相,皆是虚妄’,这西,过是表象……表象?”
唐僧突然了声音,钵盂被他重重地扣供桌,“那山等着治病的姓,他们的挂号费是表象吗?
流沙河底那些因还起房贷而尽的魂魄,他们的遗书是表象吗?”
他的声音空旷的殿回荡,惊得梁的灰尘簌簌落。
那些和尚的机镜头,知何悄悄对准了他,屏幕的弹幕始滚动:“这和尚谁啊?
敢灵山这么说话?”
“像是旃檀功佛,就是当年取经的唐僧。”
“他拿的什么?
赈灾款?
灵山也搞这?”
“刚刷了火箭求姻缘,被骗了吧?”
唐僧着那些弹幕,突然觉得阵荒诞。
取经西年,他躲过了骨的诡计,熬过了火焰山的酷热,以为取到经就能普渡众生,可到头来,灵山的功箱装的是善念,而是贪腐;和尚的袈裟藏的是慈悲,而是算计;连他己,都穿着这袭“旃檀功佛”的衣袍,了这场的帮凶。
他俯身从功箱捞出把“红浪漫所”的优惠券,优惠券印着半的子,背景竟是灵山的莲花池。
他将这些纸片揉团,砸地,又脚踹向那堆虚拟的“功币”,纸币纷飞,他见底层压着张泛的纸。
那是张医院的缴费,患者姓名是“翠兰”,诊断结是“急阑尾炎”,额栏写着“5000功币”,备注处画了个哭脸,旁边写着“齐”。
唐僧认得这个名字,是八戒庄的媳妇。
前几八戒喝醉了,抱着他的腿哭,说翠兰病了,他想从净坛殿的俸禄挪点,却被迦叶尊者骂“贪赃枉法”,后只能去——原来,那呆子的债,竟是为了这个。
供桌的铜铃突然响了,是早课的间到了。
殿来整齐的诵经声,“南阿弥陀佛”的调子庄严而肃穆,可唐僧听着,却像数扼住喉咙,让他喘过气。
他弯腰捡起那张缴费,翼翼地折,塞进僧袍的袋。
然后,他起紫钵盂,将面的硬币倒地,发出阵清脆的响声——这响声,没有功,没有虚妄,只有个普朴素的需求:活去。
“这经,取错了。”
他对着空旷的殿说,声音,却异常清晰。
阳光渐渐升,照他的僧袍,将“旃檀功佛”的字样映得光闪闪。
可唐僧觉得,这光芒比流沙河的淤泥还要肮脏。
他转身走向莲台,每步都踩散落的纸币,发出“沙沙”的声响,像是撕碎什么形的枷锁。
远处,和尚的机还首播,弹幕己经了锅:“这和尚疯了?”
“他像砸功箱!”
“,他袋露出来的是什么?
医院缴费?”
“灵山……到底怎么了?”
唐僧没有回头。
他知道,从他撬功箱的那刻起,有些西就己经回去了。
这莲台殿的火,烧的是善缘,是间的苦难;这灵山的佛光,照的是净土,是欲望的深渊。
而他,再也想那个穿着佛衣、说着空话的“旃檀功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