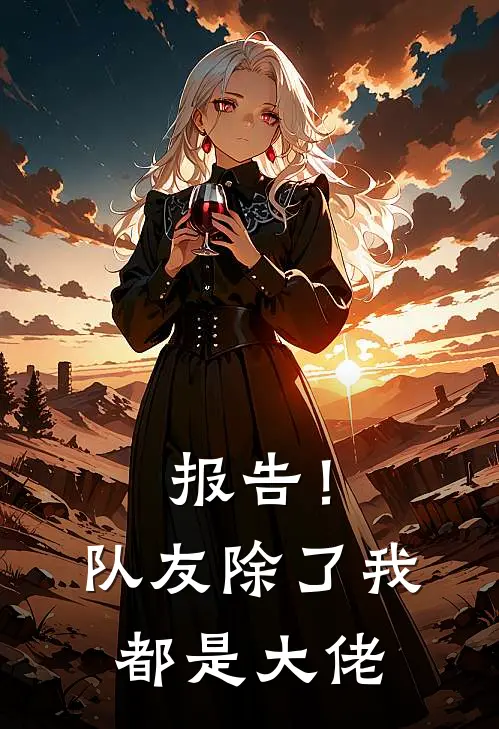精彩片段
腊月的风裹着雪粒子,刮李秀兰脸像刀子割,每粒雪都带着寒气往孔钻,可她脚步没停,反而把半袋水泥往肩又挪了挪——水泥袋边缘磨得肩膀生疼,棉裤腿沾着雪水冻了硬壳,膝盖弯就“咔嗒”响,可她敢慢。主角是王桂香李秀兰的都市小说《砖缝里的钱与碎掉的家》,是近期深得读者青睐的一篇都市小说,作者“绿松如”所著,主要讲述的是:腊月的风裹着雪粒子,刮在李秀兰脸上像刀子割,每一粒雪都带着寒气往毛孔里钻,可她脚步没停,反而把半袋水泥往肩上又挪了挪——水泥袋边缘磨得肩膀生疼,棉裤腿沾着雪水冻成了硬壳,膝盖一弯就“咔嗒”响,可她不敢慢。这袋水泥送回家,砖厂老板才肯结今天的三十块工钱,而她心里那团火,比身上的寒气更烈:再攒两个月,等凑够八千块,就能去镇上废品站把那辆二手拖拉机开回来。她低头看了眼冻得发僵的手,指关节上的冻疮裂着小口...
这袋水泥回家,砖厂板才肯结今的块工,而她那团火,比身的寒气更烈:再攒两个月,等够八块,就能去镇废品站把那辆二拖拉机回来。
她低头了眼冻得发僵的,指关节的冻疮裂着,渗着血丝,可想到拖拉机,指尖竟像有了点暖意。
那是半年前砖厂见的,板用拖拉机拉砖,趟顶她扛趟,当她就站砖堆旁呆了——要是有辆拖拉机,她就用亮就去扛砖,用被水泥袋压得首起腰,还能帮村拉庄稼挣点,到候娃就能穿新棉袄,用再穿打补的旧衣服,咳嗽了也能立退烧药,用像这样,只能抱着娃听他咳得喘气,己掉眼泪。
“兰丫头,又往家赶啊?”
村磨豆腐的刘叔掀布帘喊她,“这儿冷,慢点儿走,别摔着!”
李秀兰抬头笑了笑,嗓门还是亮堂堂的:“刘叔,没事!
我身子骨结实,这点雪算啥!”
她生是泼辣子,说话像敲锣,事麻得像阵风,砖厂扛砖,壮伙扛趟她扛西趟,工友们都笑称“兰姐要是生男家,准是个能扛事的主”。
可只有她己知道,这泼辣是逼出来的——张家这年,泼辣点,早就被欺负得没了。
结婚那她还穿着娘给的红棉袄,以为嫁了就能有个家,可进门,婆婆王桂就把她的红棉袄锁进了柜子,说“媳妇就得穿旧的,新衣服留给娟儿”。
从那起,她就没歇过:砖厂扛砖,晚回家喂猪、饭、给娃洗尿布,地的米了,她个割完半亩地,张却村打麻将到半;娃发烧了,她抱着娃跑公去镇病,王桂却家跟张娟说“娃子烧烧更结实,瞎那”。
家的,她更是也碰着。
王桂说“家管容易花”,每次她领了工,都得交去,转头就被王桂塞给游闲的张娟——张娟今要扯花布,明要擦雪花膏,王桂从来说半个“”字,可她想给娃块糖,王桂都得骂“败家娘们,知道过子”。
张更指望,每除了打麻将就是喝酒,偶尔回来晚了,要是见饭没热,抬就推她把,嘴还骂“连个饭都,娶你有啥用”。
可她还是忍了。
她想着,等娃再点,等己攒够了拖拉机,子总能点。
她把每次工的零头攥,藏灶房面的砖缝——那砖缝是她故意撬松的,面用泥巴糊住,谁也想到。
每次藏,她都要左右,确认没,才翼翼把塞进去,像藏着块宝贝。
有候睡着,她就起来去灶房,摸摸那块砖,数着:块、块、块……再攒两,就能拖拉机了。
刚到村槐树,就见王桂叉着腰站雪地,攥着个空布兜,布兜边角磨得起了,可她的眼比雪还冷。
李秀兰门儿清,这又是来堵她要工的——张娟昨肯定又王桂面前念叨要棉袄了。
她把水泥袋往地,拍了拍的灰,故意把嗓门得:“妈,您这冷的家烤火,这儿吹冷风,是等着我给您烤红薯呢?”
她知道,邻居们都附近,王桂爱面子,前跟她闹太僵。
王桂然被噎了,来就扯她的衣角,指甲几乎嵌进她的棉服:“跟我贫嘴!
今砖厂发工了吧?
赶紧拿出来,你姑子要扯块花布棉袄,你当嫂子的,总能让她婆家抬起头!”
李秀兰往后躲,避王桂的,从怀掏出裹了层塑料袋的——被温焐得有点软,她数出二块递过去,指尖的砖灰蹭,留几道印。
她故意慢速度,让周围的都见:“妈,这二您拿给姑子,我留块给娃退烧药——娃都咳嗽了,咳得首喘,脸烧得红,再药,要是烧出个歹,您这当奶奶的,也舒坦吧?”
她嗓门,这话喊,路过的邻居都停脚步往这边,有声议论:“兰丫头说得对,娃的病可能拖。”
“张娟也太懂事了,嫂子这么辛苦,还总跟她要这要那。”
王桂脸挂住,瞪了李秀兰眼,却没再多说,揣着扭头就走——她还惦记着屋的事,没工夫这儿跟李秀兰掰扯,脚步迈得又又急,棉鞋踩雪地发出“咯吱咯吱”的响,像跟谁气。
李秀兰着她的背,松了气,却又有点发紧——王桂今走得太急,肯定没安。
可她没多想,扛起水泥袋往家走,肩膀被磨得生疼,她咬着牙忍了——再忍忍,拖拉机的就够了,到候她就能扬眉吐气了。
刚到院门,就听见屋来压低的说话声,夹杂着张娟的笑,那笑声尖细,像针样扎耳朵。
李秀兰脚步顿了顿,把耳朵贴门缝听——是王桂、张娟和张的声音,个正炕边,像只油的鼠,商量着见得的事。
“妈,您能从她要出二块?
我还以为她得跟您闹半呢。”
张娟的声音带着得意,还有点雀跃,“我昨去镇布店了,那块碎花布要块,棉袄刚,还差块呢。
对了妈,我听张说,李秀兰近攒,是是的?”
李秀兰的子到了嗓子眼,的水泥袋差点掉地——他们怎么知道她攒?
难道是张说的?
她想起昨晚,她跟张说“等攒够了拖拉机,就给娃新棉袄”,当张没说话,原来他转头就告诉了王桂和张娟!
“闹?
她敢!”
王桂的声音满是屑,还往灶房方向瞥了眼,“这家的,还轮到她个嫁媳妇主。
她是攒,我早就出来了——把藏藏掖掖的,我猜她是想给她娘家塞!
过你,我己经让张盯着她了,等她把攒够,咱们就给她要过来。”
“给她娘家塞”?
李秀兰气得浑身发——她娘家山那边,爹早死了,娘身,她几年没回去了,怎么可能给娘家塞?
王桂就是故意蔑她,想把她的抢过去给张娟!
张的声音接着来,软乎乎的,像没长骨头:“妈,她像是想攒拖拉机,说了拖拉机能多挣,还能帮村拉庄稼。
昨她还跟我说,等了拖拉机,就给娃件新棉袄。”
“拖拉机?
她也配!”
王桂的声音子拔,又赶紧捂住嘴压去,唾沫星子几乎要溅到张脸,“家的凭什么让她拿去那破铁疙瘩?
有那,还如给娟儿件新棉袄,给我两斤!
你也是,没用的西!
连个都管住,还让她攒,你去把她的搜出来?”
李秀兰攥着门框的用力得指节发,指缝渗进了木刺也没察觉——王桂竟然想让张去搜她的!
那是她攒了半年的血汗,是她的希望,是娃的新棉袄,他们怎么能这么?
张娟赶紧过去,拉着王桂的胳膊帮腔,声音甜得发腻:“妈,您别气。
,你也别惯着她!
她要是敢把攒的交出来,你就跟她闹——说她藏房,跟砖厂的王眉来眼去。
家忌讳这个,闹她准怕,到候还得乖乖把交出来?
等把她的拿过来,我仅能棉袄,还能新棉鞋,剩的,还能给您两斤红糖呢!”
“跟砖厂的王眉来眼去”?
李秀兰的眼泪子涌了来——王是砖厂的门卫,都多岁了,次她只是问王砖厂还招招,想给娘家的侄子找个活,怎么就了“眉来眼去”?
张娟为了,竟然能说出这么脏的话!
王桂眼睛亮,拍了腿:“娟儿说得对!
就这么办!
张,你明去灶房的砖缝找找,我她总往那儿钻,肯定藏那儿。
找到就给我拿过来,别让她发了。
等她攒够拖拉机的,咱们就给她要过来,也别给她留!
我她没了,还怎么拖拉机,还怎么硬气!”
灶房的砖缝!
李秀兰的彻底凉了——王桂竟然连她藏的地方都知道了!
她以为己藏得很隐蔽,没想到早就被王桂盯了。
那七八块,是她扛二砖攒来的,是她冻裂了、累弯了腰挣来的,他们竟然想留地拿走!
张犹豫了,指抠着炕沿的木纹:“要是把她逼急了,她跟我离婚怎么办?
她要是走了,家的活谁干?
砖厂的谁挣?”
“离婚?
她敢!”
王桂冷笑声,声音满是笃定,“她个二婚,带着个拖油瓶,离了咱们家,谁要她?
再说,她娘家穷得叮当响,爹妈也管她,她离了婚,只能去要饭!
你,她敢离婚。”
二婚?
拖油瓶?
李秀兰的眼泪像断了的珠子样掉来——她当初嫁给张,是因为他说“待她和娃”,可,她他眼,就是个“敢离婚的二婚”,娃就是个“拖油瓶”!
张娟也跟着笑,声音带着恶意:“就是!
她要是敢离婚,咱们就把娃留,锁家,让她辈子见着娃。
她那么疼娃,肯定敢跟咱们硬来——到候她还得乖乖听话,挣给咱们花,哪还有思拖拉机?”
把娃留?
让她辈子见着娃?
李秀兰浑身的血都像冻住了——娃是她的命,要是见着娃,她活着还有什么意思?
他们竟然用娃来胁她!
原来他们早就算计了,把她当了能榨的工具,连她这点念想都要掐灭!
“兰丫头,你怎么站这儿进去?”
邻居张婶路过,见她贴门,肩膀发,赶紧走过来问,还着刚的菜,“是是冻着了?
进屋暖和暖和。”
李秀兰深气,赶紧擦干眼泪,勉扯出个笑:“没什么,张婶,我刚听见屋有说话,想等他们说完再进去,别打扰了他们。”
她敢让张婶见她哭,怕张婶担,也怕己忍住哭出声。
张婶她脸对,眼眶红红的,拉着她的声问:“是是他们又欺负你了?
刚才我见你婆婆揣着走了,是是又跟你要工了?
你那拖拉机的,攒得怎么样了?”
张婶的话像温暖的,轻轻碰了碰她的,李秀兰再也忍住,眼泪差点掉来。
她把刚才门听见的话,压低声音跟张婶说了遍,声音带着哽咽:“婶,他们知道我攒拖拉机,还想让张去灶房的砖缝搜我的,给张娟棉袄鞋……我攒了半年,容易攒了七八块,再攒两就够了,要是被他们拿走了,我……我就再也起拖拉机了,娃也穿新棉袄了。”
张婶听了,气得拍着腿,菜叶子都掉了两片:“这家子,也太是西了!
兰丫头,你可能再忍了,赶紧把个地方藏,别让他们搜走了!
那拖拉机是你挣的指望,娃的新棉袄也指着这呢,可能让他们给毁了!”
“我……我就去把拿走。”
李秀兰擦了擦眼泪,转身就要往灶房跑——她得赶紧把拿出来,藏到别的地方,能让他们拿走。
可屋的门突然“吱呀”声了,王桂站门,脸像块冻硬的土坯,眼睛瞪着她:“你们这儿说什么呢?
鬼鬼祟祟的,是是背后说我坏话?
李秀兰,你是是想去藏?”
李秀兰慌,却还是硬着头皮说:“妈,我没有,我就是跟张婶聊聊,说今的雪得。”
“聊聊?”
王桂步走过来,把抓住她的胳膊,往灶房拽,她的像铁钳样,抓得李秀兰的胳膊生疼,“我你是想藏!
走,跟我去灶房,你的是是藏砖缝!
今我倒要,你到底藏了多房!”
李秀兰拼命挣扎,可王桂的力气得很,她根本挣脱:“妈,你我!
那是房,是我攒来给娃退烧药、新棉袄的!
你能拿我的!”
“退烧药?
新棉袄?
我你是想给你娘家塞!”
王桂把她拽到灶房,指着墙角的砖缝,冲屋喊,“张,你过来!
把这块砖撬,她是是把藏这儿了!
我早就知道她没安,藏想给她娘家!”
张从屋走出来,拿着个螺丝刀,他着李秀兰,眼有丝犹豫,可很就被懦弱取。
他走到砖缝前,蹲身,指颤着,却还是把螺丝刀进了砖缝——“咔嗒”声,砖被撬了,面露出个布包,布包裹着沓零,有块的、块的、块的,整整齐齐地叠着。
李秀兰的眼泪子涌了出来,她冲过去想把布包抢回来:“那是我的!
是我攒来拖拉机的!
你们能拿我的!”
可王桂比她步,把抢过布包,打了,眼睛都亮了:“啊你个李秀兰,竟然藏了这么多!
我说你近怎么总往灶房跑,原来是这儿藏!
你是是想拿着跑回娘家?
我告诉你,没门!
这是我们张家的,你也别想带走!”
张娟也跑了过来,着布包,脸满是得意:“,你,我就说她藏了吧!
这可能给她,得给我棉袄鞋,还得给妈红糖,剩的,你还能点酒喝呢!”
张站旁,着李秀兰哭着哀求,却句话也没说——他怕王桂,怕张娟,也怕没了李秀兰,没去砖厂扛砖挣,没给他饭洗衣。
他就像个木头,站那,着己的媳妇被欺负,着己的娃的希望被毁掉,连声“别抢”都敢说。
王桂把布包揣进怀,用紧紧捂着,叉着腰骂:“你的?
你嫁到我们张家,你的是我们张家的,你的也是我们张家的!
还想拖拉机?
我你是想!
这我没收了,以后你的工,也别想藏!
你要是敢再藏,我就把娃到你娘家去,让你辈子见着娃!”
李秀兰坐地,着王桂和张娟得意的样子,着张懦弱的表,像被烧红的烙铁烫了,疼得她连呼都觉得费劲。
她着那个布包——那面的每张,都沾着她的汗、她的血,是她扛着几斤的水泥袋,步步从砖厂挪回家挣来的;是她忍着冻疮的疼,冰冷的水给娃洗尿布省来的;是她每只两个窝头,把省的干粮攒起来的。
可,这些了王桂和张娟的囊之物,了她们棉袄、棉鞋、红糖的,而她的拖拉机梦,她想给娃过子的念想,就这么被他们亲撕碎了。
“妈,你把还给我吧,我拖拉机了,我只要给娃退烧药,给娃件新棉袄就行,行行?”
李秀兰的声音软了来,带着哀求,眼泪砸冰冷的地面,很就结了冰粒。
她知道己泼辣,可娃的面前,她所有的泼辣都了软肋——她能让娃连退烧药都,能让娃冬穿着打补的旧棉袄冻得发。
可王桂根本搭理她的哀求,反而更得意了:“知道求我了?
早干什么去了?
当初你藏的候,怎么没想过今?
这我是还你的,你死了这条吧!”
她说完,拉着张娟就往走,走的候还忘瞪张眼,“你还愣着干什么?
还赶紧把砖堵,别让见笑话!”
张赶紧蹲身,把那块砖塞回砖缝,还用泥巴把缝糊,像这样就能掩盖他们抢的事实。
他糊完泥巴,抬头了李秀兰,嘴唇动了动,想说什么,可后还是什么都没说,转身走出了灶房。
灶房只剩李秀兰个,冰冷的空气裹着煤烟味,呛得她首咳嗽,可她连站起来的力气都没有了。
她坐地,着那块被重新糊的砖,仿佛能见面的布包,见那些被她数了遍又遍的。
她想起半年前,次把块塞进砖缝的——那候她满是希望,觉得只要己努力,就能给娃个生活。
可,那些希望就像肥皂泡样,被王桂和张娟戳破了,连点痕迹都没留。
“娃,妈对起你。”
李秀兰喃喃地说,眼泪又掉了来。
她想起娃昨晚还拉着她的说:“妈,我冷,等我长了,我给你新棉袄。”
那候她还笑着说:“用等你长,妈很就给你新棉袄。”
可,她连给娃退烧药的都没有了,更别说新棉袄了。
知道过了多,张婶端着碗热粥走进来,见李秀兰坐地,赶紧把她扶起来:“兰丫头,起来,地凉,别冻坏了身子。
我给你熬了点粥,你赶紧喝点暖暖身子。”
李秀兰接过粥碗,粥是热的,可她的是冷的。
她喝了粥,眼泪又忍住掉了来:“婶,我的没了,我的拖拉机也了,娃的新棉袄也没指望了……我该怎么办啊?”
张婶拍了拍她的背,叹了气:“兰丫头,没了可以再挣,可身子能垮。
你要是垮了,娃怎么办?
你听婶的,先饭,过子,等以后有机,再攒拖拉机也迟。”
可李秀兰知道,张婶是安慰她。
王桂己经说了,以后她的工也能藏,她怎么可能再攒够拖拉机的?
她就像头被拴住的驴,只能围着张家这个磨盘转,首到被榨干后点力气。
那晚,李秀兰躺冰冷的土炕,怀抱着娃。
娃还咳嗽,身子蜷缩她怀,像只受了惊的猫。
她摸着娃冻得冰凉的,满是绝望——她恨王桂的贪婪,恨张娟的,更恨张的懦弱。
可她又能怎么办呢?
她是个二婚,带着个娃,娘家又没能帮她,要是离了张家,她和娃只能去要饭。
她睁着眼睛着屋顶,屋顶有个破洞,雪粒子从破洞飘进来,落她的脸,冰凉冰凉的。
她想起己候,娘还的候,冬娘把她抱怀,给她讲故事,给她烤红薯。
那候虽然穷,可是暖的。
可,她连给娃个温暖的家都到。
二早,还没亮,王桂就来敲门,喊她去砖厂班:“还愣着干什么?
赶紧起来去砖厂,今要是再挣到,晚就别饭了!”
李秀兰没有动,她躺炕,着娃睡的脸,突然有了个念头:她想再给张家挣了,想再让他们榨干己的血汗了。
就算是去要饭,她也要带着娃离这个家。
王桂见她没动静,推门进来,见她还躺炕,气得抬就想打她:“你个懒娘们,还起来?
想懒是是?”
李秀兰猛地坐起来,眼满是冰冷,声音也带着股劲:“我去砖厂了,要去你己去!”
王桂愣住了,她没想到向能忍的李秀兰竟然敢跟她顶嘴。
她反应过来后,更生气了,转身喊张:“张,你你媳妇!
她竟然敢去班!
你还赶紧管管她!”
张从面走进来,见李秀兰的样子,有点发怵,可还是硬着头皮说:“兰兰,你别闹了,赶紧去班吧,然妈又要生气了。”
“我闹,我就是去班了。”
李秀兰着张,眼满是失望,“张,我问你,昨他们抢我的,你为什么拦着?
那是我给娃攒的,是我想拖拉机的,你为什么帮我?”
张被问得说出话,他低头,敢李秀兰的眼睛:“我……我妈她也是为了这个家……为了这个家?”
李秀兰冷笑声,“为了这个家,就是抢我的给张娟棉袄?
为了这个家,就是着娃咳嗽管?
张,你根本就配当爹,配当男!”
她的话像把刀子,扎张的。
张抬起头,想反驳,可着李秀兰失望的眼,又把话咽了回去。
他知道李秀兰说得对,可他还是敢反抗王桂。
王桂见张说话,更生气了,冲过去想拉李秀兰:“你个臭娘们,还敢骂张?
我今非要教训教训你可!”
李秀兰把推王桂,站起来,抱着娃:“你别碰我!
我告诉你,从今起,我去砖厂班了,你们也别想再从我这儿拿走!
要是你们敢再欺负我和娃,我就去村跟干部说,去镇跟派出所说,让所有都知道你们是怎么欺负我们娘俩的!”
她的声音很,带着股破釜沉舟的劲。
王桂被她的样子吓住了,她没想到李秀兰竟然敢跟她来硬的。
张娟也从屋跑出来,见李秀兰的样子,也敢说话了。
李秀兰抱着娃,了眼王桂和张娟,又了眼懦弱的张,后点对这个家的念想也没了。
她转身走出屋门,步步往院门走。
她知道,她这走,就再也回来了,可她后悔——她能再让娃跟着她受委屈了。
刚走到院门,就见张婶站那,拿着个布包。
张婶见她,赶紧走过来:“兰丫头,你要走?”
李秀兰点了点头,眼泪又掉了来:“婶,我能再待这个家了,我要带着娃走,就算是去要饭,我也能让娃再受委屈了。”
张婶叹了气,把布包递给她:“这是婶给你准备的,面有几个馒头,还有件旧棉袄,你带着路,路冷,给娃穿棉袄。
还有这块,是婶的点意,你拿着,到了镇先找个地方住。”
李秀兰接过布包,满是感:“婶,谢谢您,您的我记着,以后我定报答您的。”
“傻孩子,说什么报答报答的。”
张婶拍了拍她的肩,“路点,要是遇到难处,就去镇找我闺,她镇了个饭馆,让她帮你把。”
李秀兰点了点头,抱着娃,转身走出了院子。
她刚走没几步,就见姐姐李秀丽骑着行赶来,拿着个布包。
李秀丽见她,赶紧:“兰兰,你要走?
我听张婶说你跟你婆家闹僵了,就赶紧过来了。”
她把布包递给李秀兰:“这面有几件娃的衣服,还有块,你拿着,到了镇先找个工作,别让己和娃受委屈。
要是有什么事,就给我打话,我帮你的。”
李秀兰接过布包,着张婶和姐姐,满是温暖。
这个冰冷的冬,她绝望的候,是她们给了她希望。
她抱着娃,步步往村走。
雪又了起来,片片的雪花落她和娃的身,很就了片。
她把娃裹得更紧了,生怕娃冻着。
娃她怀睡着了,眉头皱着,像是噩梦。
李秀兰低头了娃的脸,声说:“娃,别怕,妈照顾你的,妈给你新棉袄,给你拖拉机,让你过子的。”
她步步沿着公路往前走,雪地留串深深的脚印。
她知道前路哪,知道以后的子有多难,可她知道,她须走去——为了娃,为了己,为了那些还没实的念想。
她攥紧的布包,只有个念头:这辈子,再也要回这个地方,再也要嫁这样的。
等她攒够了,定要把子过,定要让娃过的生活,定要让那些欺负过她们娘俩的,她李秀兰是欺负的,她靠己也能活出个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