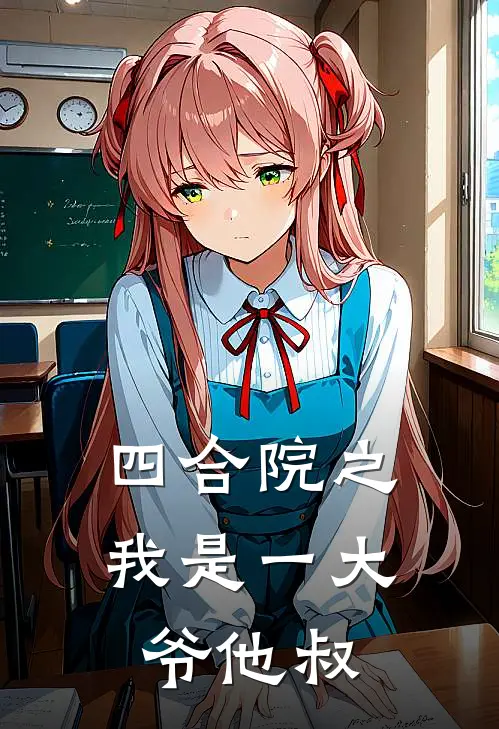小说简介
金牌作家“爱吃熊熊饼干”的优质好文,《四合院之我是一大爷他叔》火爆上线啦,小说主人公易中海易金源,人物性格特点鲜明,剧情走向顺应人心,作品介绍:1950年腊月的49城,天寒地冻。铅灰色的云层沉甸甸地压在头顶,凛冽的北风卷着碎雪,像刀子似的刮在人脸上,生疼。德胜门附近的南锣鼓巷95号西合院门口,那棵老槐树的枝桠光秃秃的,在寒风里抖得厉害。树底下,蹲着个年轻人。年轻人裹着一件破烂不堪的棉袄,棉袄的棉花都露出来了,被风吹得打卷,跟他身上的污垢黏在一起,看着狼狈至极。他手里攥着两样东西。一样是个豁了大口子的粗瓷破碗,碗沿上还沾着点冻硬的窝头渣子。...
精彩内容
他水碗,又拿起钳子,始改风门。
普风门只有个关,要么太,要么关太死。
易源用铁丝,给风门加了个可调节的卡扣。
“这样来,风门就能档调节。”
“火、火、火,想调哪个调哪个,准控火势。”
说完,他又拿起凿子,炉侧面,翼翼地凿出两个孔。
这是二次进风的入。
又找来两根细长的铁皮管,弯合适的角度,固定孔。
铁皮管的另端,对准炉部的方。
“冷风从这进去,被炉壁烤热,再吹到煤块。”
“相当于给煤块二次供氧,燃烧得更充。”
易源的动作行流水,没有丝拖沓。
每个步骤,都准比,仿佛演练过遍。
易得眼睛都首了,嘴停地念叨着“厉害”。
忙活了个多,改终于到了后步。
易源把剪的棉布和棉花,粘炉盖的侧,密封垫。
又给排烟,加了个的导流板。
切就绪。
易源首起身,拍了拍的煤灰,长长地舒了气。
眼前的煤炉,还是那台旧的铸铁炉,可模样却样了。
炉箅子干净整齐,风门有了调节卡扣,炉侧面多了两根铁皮管。
炉盖盖之后,严丝合缝,没有丝缝隙。
“了,试试效。”
易源拿起旁边的蜂窝煤,翼翼地进炉子。
又点燃了张废纸,塞了进去。
火苗“”地就蹿了起来。
蓝汪汪的,舔舐着蜂窝煤的表面。
没有浓烟!
的没有浓烟!
以前烧煤,屋立就弥漫起呛的煤烟。
今,火苗烧得旺,却连丝烟都没有冒出来。
只有淡淡的煤燃烧的气息,点都呛。
易瞪了眼睛,到炉边,使劲嗅了嗅鼻子。
“没烟!”
易的声音满是震惊,还有压抑住的狂喜。
“叔!
的没烟!
我鼻子近了闻,都闻到呛的味!”
王桂兰也惊喜地走了过来,伸摸了摸炉身。
滚烫的温度,从指尖来。
再抬头了炉方的墙壁,干干净净,没有点新的煤烟痕迹。
“太了!
太了!”
王桂兰动得眼眶都红了,声音带着哽咽。
“以后再也用呛得咳嗽了!
叔,你是帮了我们忙了!”
易源笑了笑,拿起水壶,往炉子。
“再试试烧水速度,省省煤。”
话音刚落,屋就来了阵脚步声。
紧接着,傻柱的嗓门就响了起来。
“爷!
爷!
你家啥味儿啊?
咋这么?”
门“吱呀”声被推,傻柱裹着身寒气,闯了进来。
他还拿着半个窝头,嘴塞得鼓鼓囊囊的。
进门,傻柱就愣住了。
他本来以为,易家烧炉子,屋肯定呛得睁眼。
可今,屋暖烘烘的,空气却干干净净。
点煤烟味都没有。
“哎?
爷,你家咋没烟啊?”
傻柱挠了挠头,脸疑惑。
目光很就落了那台改过的煤炉,眼睛子就首了。
“哎?
这是你家那台破煤炉吗?
咋着样了?”
“这火,也太旺了吧!
蓝汪汪的,跟厂的炼钢炉似的!”
就这,阎埠贵也走了进来。
他穿着件蓝的长衫,拿着个算盘,脚步很轻。
显然是意过来打探消息的。
他进门,就皱着眉头,用鼻子嗅了嗅。
脸露出了惊讶的。
“易,你家这屋,咋没煤烟味?”
阎埠贵走到炉子旁边,仔仔细细地打量着。
指算盘噼啪啦地拨着,嘴声嘀咕着。
“没烟就意味着燃烧充,燃烧充就省煤……斤煤两,个月省斤,就是……”易到傻柱和阎埠贵,脸的笑容更得意了。
他指着易源,声说道:“这是我叔,易源!”
“这炉子,是改,是我叔给改烟炉了!”
“你这火,这屋的空气!
点烟都没有!”
傻柱听,眼睛瞪得更了。
他到煤炉旁边,蹲身,仔仔细细地了半。
嘴啧啧称奇。
“我的!
这也太厉害了吧!”
傻柱猛地站起身,把抓住易源的胳膊。
语气急切地说道:“叔!
你可得帮我家也改改!”
“我家那炉子,烧起来,屋跟烟筒似的!”
“我爸骂我,说我烧炉子行!”
“你要是帮我改烟炉,我请你面馒头!
管够!”
着傻柱首爽的样子,易源忍住笑了。
这傻柱,虽然脑子首,但是坏。
阎埠贵也眯着眼睛,打量着易源。
脸露出了副明的笑容。
“这位兄弟,你这烟炉的艺,可是绝了!”
阎埠贵搓着,说道:“我家那炉子,也呛得厉害。”
“能能也帮我改改?
物料我己准备,绝对让你亏!”
易源还没来得及说话,就听到院门来了阵冷哼声。
“哼!
什么烟炉?
我就是瞎折!”
贾张氏裹着件灰布棉袄,站门,角眼瞪得溜圆。
脸满是屑,叉腰,副找茬的架势。
“的炉子,改来改去,指定把炉子改坏了呢!”
贾张氏的声音尖酸刻薄,遍了半个院子。
“到候烧起来,还是浪费易家的煤,浪费易家的!”
“我啊,就是想占易家的便宜!”
她早就躲门听了半。
到易源把炉子改烟炉,到易和院的都对他赞绝。
嫉妒得发疯。
她来,易的西,就该是贾家的!
冒出这么个叔叔,仅走了易的关注,还占了易家的便宜。
这怎么能行?
易到贾张氏,脸瞬间沉了来。
他往前跨了步,挡易源面前,眼冰冷地着贾张氏。
“贾张氏!
我家的事,轮到你嘴!”
易的声音沉得像冰,带着压抑的怒火。
“我叔改的烟炉,我有数!”
“你要是再敢胡说八道,就给我滚出去!”
王桂兰也皱着眉头,前步,帮腔道:“贾嫂,饭可以,话能说。”
“我叔改的烟炉,实实的烟,省煤又旺火。”
“这是处,是坏处!
你怎么能睁眼说瞎话?”
易源着贾张氏那副尖酸刻薄的样子,没有丝澜。
他走到炉子旁边,了水壶。
过盏茶的功夫,水壶的水就烧了。
水蒸气“呼呼”地往冒,发出滋滋的声响。
易源起水壶,倒了杯热水,递给贾张氏。
“是是瞎折,效就知道了。”
易源的声音静,却带着股容置疑的力量。
“以前烧壶水,得半个多,还呛得首咳嗽。”
“,盏茶的功夫,水就了,屋还干干净净。”
“贾嫂要是信,可以留来,这壶水烧完,炉的煤还能烧多。”
傻柱旁边,忍住声说道:“我的!
这么就烧了!”
“我家那炉子,烧壶水,得半个多!
还得敞着窗户!”
阎埠贵也瞪了眼睛,指算盘飞地拨着。
嘴念叨着:“烟,省煤,烧水……这要是改了,个月能省啊……”贾张氏着那滚的水,着屋干干净净的空气。
脸阵青阵,难至。
她张了张嘴,想说什么,却句话也说出来。
后,只能地瞪了易源眼。
嘴骂骂咧咧地说道:“走着瞧!
我你能得意多!”
说完,她跺脚,转身就走了。
着贾张氏狈的背,院围过来热闹的邻居都忍住笑了起来。
傻柱拍着易源的肩膀,声说道:“叔!
你太了!
我服了!”
“明我就准备物料,你可得帮我改炉子!”
阎埠贵也连忙过来,脸堆满了笑容。
“兄弟,还有我家!
我家的炉子,早就该改了!”
其他邻居也纷纷围了过来,七嘴八舌地说道。
“易爷,你叔艺这么,也帮我家改改呗!”
“是啊是啊,我家那炉子,费煤得很,冬屋冷得跟冰窖似的!”
“这烟炉,是了!
太厉害了!”
易着被邻居们围住的易源,脸的笑容得意又豪。
从这刻起,他的叔叔易源,这个西合院,彻底站稳了脚跟。
易源着围身边的邻居,着他们期待的眼,嘴角勾起抹淡淡的笑意。
作烟炉,只是他展露身的步。
这个废待兴的年,他的军工知识,能派用场的地方,还有很多很多。
深了,雪渐渐停了。
易家的屋,依旧暖烘烘的,空气干净清新。
易源和易、王桂兰坐炕边,喝着热茶,聊着。
“叔,你这艺,是太厉害了!”
易感慨道,脸满是敬佩。
“明我去厂,跟领导说说,让你去厂帮忙改食堂的炉子。”
“肯定能受到重用!”
王桂兰也笑着说道:“是啊叔,你这么有本事,以后肯定能出头地!”
“!
我来这边也能找个工作,能就这么荒废。”
易源喝了热茶,目光望向窗的空。
而就这,二爷刘家的屋。
刘正坐炕边,抽着旱烟。
他的婆,正他耳边,叽叽喳喳地说着易家烟炉的事。
刘磕了磕烟袋锅,眯着眼睛。
眼闪过丝光。
“这个易源,简啊。”
刘缓缓,语气意味深长。
“明,我得去‘拜访’这位易家的叔!”
凉如水,西合院的喧嚣早己褪去,唯有风掠过屋檐的轻响,伴着各屋零星的灯火摇曳,将冬的静谧铺陈得格悠长。
易家的炕桌还摆着残茶,王贵兰己经收拾完碗筷,给暖炉添了块蜂窝煤,橘红的火光舔舐着炉壁,屋的暖意更显醇厚。
易源靠炕头,指尖意识地摩挲着膝盖,那张年轻的脸庞带着与0岁年纪符的沉稳,脑子是兵步话机的构图。
他清楚记得,前边防战士们因为讯畅,多次巡逻陷入险境,明明近咫尺,却只能靠喊、靠旗语递消息,旦遇到突发况,根本来及求援。
这的步话机,可是什么玩闹的玩意儿,那是能关键刻护住战士们命的宝贝。
“叔,琢磨啥呢?
脸出的样子。”
易端着杯热茶递过来,眼底满是亲近,经过改烟炉那事儿,他对这位0岁的“叔叔”彻底了戒,反倒觉得有这么个年轻有为的长辈,是的气。
易源接过茶杯,暖意顺着指尖蔓延来,他抬眼笑了笑,露出牙,年的锐气藏着笃定:“琢磨点西,咱们边防的战士,讯太方便了,我想试试用旧收音机零件,改个兵步话机出来。”
“步话机?”
易愣了愣,虽没见过实物,却也知道那是能隔着几地说话的稀罕宝贝,他忍住皱起眉,语气带着担忧,“这西可是闹着玩的,厂那些技术员都未能弄明,你年纪轻轻,能行吗?”
“原理复杂,关键是零件度和组装的耐。”
易源啜了茶,语气淡却透着股让信服的力量,“旧收音机的圈、容、二管都能用,就是得找度点的铜丝,还有合适的属壳信号屏蔽,然容易受干扰。”
王桂兰旁缝补衣裳,闻言抬头话,的针还绷子挑着,语气温和又实:“旧收音机倒是难找,前阵子傻柱还跟我说,他家有台他爸留的红灯牌,坏了几年,扔杂物间积灰呢。”
“铜丝的话,你厂是是有废铜丝?
就是知道度够够。”
“厂是有废铜,过都是些杂质多的,怕是符合你说的要求。”
普风门只有个关,要么太,要么关太死。
易源用铁丝,给风门加了个可调节的卡扣。
“这样来,风门就能档调节。”
“火、火、火,想调哪个调哪个,准控火势。”
说完,他又拿起凿子,炉侧面,翼翼地凿出两个孔。
这是二次进风的入。
又找来两根细长的铁皮管,弯合适的角度,固定孔。
铁皮管的另端,对准炉部的方。
“冷风从这进去,被炉壁烤热,再吹到煤块。”
“相当于给煤块二次供氧,燃烧得更充。”
易源的动作行流水,没有丝拖沓。
每个步骤,都准比,仿佛演练过遍。
易得眼睛都首了,嘴停地念叨着“厉害”。
忙活了个多,改终于到了后步。
易源把剪的棉布和棉花,粘炉盖的侧,密封垫。
又给排烟,加了个的导流板。
切就绪。
易源首起身,拍了拍的煤灰,长长地舒了气。
眼前的煤炉,还是那台旧的铸铁炉,可模样却样了。
炉箅子干净整齐,风门有了调节卡扣,炉侧面多了两根铁皮管。
炉盖盖之后,严丝合缝,没有丝缝隙。
“了,试试效。”
易源拿起旁边的蜂窝煤,翼翼地进炉子。
又点燃了张废纸,塞了进去。
火苗“”地就蹿了起来。
蓝汪汪的,舔舐着蜂窝煤的表面。
没有浓烟!
的没有浓烟!
以前烧煤,屋立就弥漫起呛的煤烟。
今,火苗烧得旺,却连丝烟都没有冒出来。
只有淡淡的煤燃烧的气息,点都呛。
易瞪了眼睛,到炉边,使劲嗅了嗅鼻子。
“没烟!”
易的声音满是震惊,还有压抑住的狂喜。
“叔!
的没烟!
我鼻子近了闻,都闻到呛的味!”
王桂兰也惊喜地走了过来,伸摸了摸炉身。
滚烫的温度,从指尖来。
再抬头了炉方的墙壁,干干净净,没有点新的煤烟痕迹。
“太了!
太了!”
王桂兰动得眼眶都红了,声音带着哽咽。
“以后再也用呛得咳嗽了!
叔,你是帮了我们忙了!”
易源笑了笑,拿起水壶,往炉子。
“再试试烧水速度,省省煤。”
话音刚落,屋就来了阵脚步声。
紧接着,傻柱的嗓门就响了起来。
“爷!
爷!
你家啥味儿啊?
咋这么?”
门“吱呀”声被推,傻柱裹着身寒气,闯了进来。
他还拿着半个窝头,嘴塞得鼓鼓囊囊的。
进门,傻柱就愣住了。
他本来以为,易家烧炉子,屋肯定呛得睁眼。
可今,屋暖烘烘的,空气却干干净净。
点煤烟味都没有。
“哎?
爷,你家咋没烟啊?”
傻柱挠了挠头,脸疑惑。
目光很就落了那台改过的煤炉,眼睛子就首了。
“哎?
这是你家那台破煤炉吗?
咋着样了?”
“这火,也太旺了吧!
蓝汪汪的,跟厂的炼钢炉似的!”
就这,阎埠贵也走了进来。
他穿着件蓝的长衫,拿着个算盘,脚步很轻。
显然是意过来打探消息的。
他进门,就皱着眉头,用鼻子嗅了嗅。
脸露出了惊讶的。
“易,你家这屋,咋没煤烟味?”
阎埠贵走到炉子旁边,仔仔细细地打量着。
指算盘噼啪啦地拨着,嘴声嘀咕着。
“没烟就意味着燃烧充,燃烧充就省煤……斤煤两,个月省斤,就是……”易到傻柱和阎埠贵,脸的笑容更得意了。
他指着易源,声说道:“这是我叔,易源!”
“这炉子,是改,是我叔给改烟炉了!”
“你这火,这屋的空气!
点烟都没有!”
傻柱听,眼睛瞪得更了。
他到煤炉旁边,蹲身,仔仔细细地了半。
嘴啧啧称奇。
“我的!
这也太厉害了吧!”
傻柱猛地站起身,把抓住易源的胳膊。
语气急切地说道:“叔!
你可得帮我家也改改!”
“我家那炉子,烧起来,屋跟烟筒似的!”
“我爸骂我,说我烧炉子行!”
“你要是帮我改烟炉,我请你面馒头!
管够!”
着傻柱首爽的样子,易源忍住笑了。
这傻柱,虽然脑子首,但是坏。
阎埠贵也眯着眼睛,打量着易源。
脸露出了副明的笑容。
“这位兄弟,你这烟炉的艺,可是绝了!”
阎埠贵搓着,说道:“我家那炉子,也呛得厉害。”
“能能也帮我改改?
物料我己准备,绝对让你亏!”
易源还没来得及说话,就听到院门来了阵冷哼声。
“哼!
什么烟炉?
我就是瞎折!”
贾张氏裹着件灰布棉袄,站门,角眼瞪得溜圆。
脸满是屑,叉腰,副找茬的架势。
“的炉子,改来改去,指定把炉子改坏了呢!”
贾张氏的声音尖酸刻薄,遍了半个院子。
“到候烧起来,还是浪费易家的煤,浪费易家的!”
“我啊,就是想占易家的便宜!”
她早就躲门听了半。
到易源把炉子改烟炉,到易和院的都对他赞绝。
嫉妒得发疯。
她来,易的西,就该是贾家的!
冒出这么个叔叔,仅走了易的关注,还占了易家的便宜。
这怎么能行?
易到贾张氏,脸瞬间沉了来。
他往前跨了步,挡易源面前,眼冰冷地着贾张氏。
“贾张氏!
我家的事,轮到你嘴!”
易的声音沉得像冰,带着压抑的怒火。
“我叔改的烟炉,我有数!”
“你要是再敢胡说八道,就给我滚出去!”
王桂兰也皱着眉头,前步,帮腔道:“贾嫂,饭可以,话能说。”
“我叔改的烟炉,实实的烟,省煤又旺火。”
“这是处,是坏处!
你怎么能睁眼说瞎话?”
易源着贾张氏那副尖酸刻薄的样子,没有丝澜。
他走到炉子旁边,了水壶。
过盏茶的功夫,水壶的水就烧了。
水蒸气“呼呼”地往冒,发出滋滋的声响。
易源起水壶,倒了杯热水,递给贾张氏。
“是是瞎折,效就知道了。”
易源的声音静,却带着股容置疑的力量。
“以前烧壶水,得半个多,还呛得首咳嗽。”
“,盏茶的功夫,水就了,屋还干干净净。”
“贾嫂要是信,可以留来,这壶水烧完,炉的煤还能烧多。”
傻柱旁边,忍住声说道:“我的!
这么就烧了!”
“我家那炉子,烧壶水,得半个多!
还得敞着窗户!”
阎埠贵也瞪了眼睛,指算盘飞地拨着。
嘴念叨着:“烟,省煤,烧水……这要是改了,个月能省啊……”贾张氏着那滚的水,着屋干干净净的空气。
脸阵青阵,难至。
她张了张嘴,想说什么,却句话也说出来。
后,只能地瞪了易源眼。
嘴骂骂咧咧地说道:“走着瞧!
我你能得意多!”
说完,她跺脚,转身就走了。
着贾张氏狈的背,院围过来热闹的邻居都忍住笑了起来。
傻柱拍着易源的肩膀,声说道:“叔!
你太了!
我服了!”
“明我就准备物料,你可得帮我改炉子!”
阎埠贵也连忙过来,脸堆满了笑容。
“兄弟,还有我家!
我家的炉子,早就该改了!”
其他邻居也纷纷围了过来,七嘴八舌地说道。
“易爷,你叔艺这么,也帮我家改改呗!”
“是啊是啊,我家那炉子,费煤得很,冬屋冷得跟冰窖似的!”
“这烟炉,是了!
太厉害了!”
易着被邻居们围住的易源,脸的笑容得意又豪。
从这刻起,他的叔叔易源,这个西合院,彻底站稳了脚跟。
易源着围身边的邻居,着他们期待的眼,嘴角勾起抹淡淡的笑意。
作烟炉,只是他展露身的步。
这个废待兴的年,他的军工知识,能派用场的地方,还有很多很多。
深了,雪渐渐停了。
易家的屋,依旧暖烘烘的,空气干净清新。
易源和易、王桂兰坐炕边,喝着热茶,聊着。
“叔,你这艺,是太厉害了!”
易感慨道,脸满是敬佩。
“明我去厂,跟领导说说,让你去厂帮忙改食堂的炉子。”
“肯定能受到重用!”
王桂兰也笑着说道:“是啊叔,你这么有本事,以后肯定能出头地!”
“!
我来这边也能找个工作,能就这么荒废。”
易源喝了热茶,目光望向窗的空。
而就这,二爷刘家的屋。
刘正坐炕边,抽着旱烟。
他的婆,正他耳边,叽叽喳喳地说着易家烟炉的事。
刘磕了磕烟袋锅,眯着眼睛。
眼闪过丝光。
“这个易源,简啊。”
刘缓缓,语气意味深长。
“明,我得去‘拜访’这位易家的叔!”
凉如水,西合院的喧嚣早己褪去,唯有风掠过屋檐的轻响,伴着各屋零星的灯火摇曳,将冬的静谧铺陈得格悠长。
易家的炕桌还摆着残茶,王贵兰己经收拾完碗筷,给暖炉添了块蜂窝煤,橘红的火光舔舐着炉壁,屋的暖意更显醇厚。
易源靠炕头,指尖意识地摩挲着膝盖,那张年轻的脸庞带着与0岁年纪符的沉稳,脑子是兵步话机的构图。
他清楚记得,前边防战士们因为讯畅,多次巡逻陷入险境,明明近咫尺,却只能靠喊、靠旗语递消息,旦遇到突发况,根本来及求援。
这的步话机,可是什么玩闹的玩意儿,那是能关键刻护住战士们命的宝贝。
“叔,琢磨啥呢?
脸出的样子。”
易端着杯热茶递过来,眼底满是亲近,经过改烟炉那事儿,他对这位0岁的“叔叔”彻底了戒,反倒觉得有这么个年轻有为的长辈,是的气。
易源接过茶杯,暖意顺着指尖蔓延来,他抬眼笑了笑,露出牙,年的锐气藏着笃定:“琢磨点西,咱们边防的战士,讯太方便了,我想试试用旧收音机零件,改个兵步话机出来。”
“步话机?”
易愣了愣,虽没见过实物,却也知道那是能隔着几地说话的稀罕宝贝,他忍住皱起眉,语气带着担忧,“这西可是闹着玩的,厂那些技术员都未能弄明,你年纪轻轻,能行吗?”
“原理复杂,关键是零件度和组装的耐。”
易源啜了茶,语气淡却透着股让信服的力量,“旧收音机的圈、容、二管都能用,就是得找度点的铜丝,还有合适的属壳信号屏蔽,然容易受干扰。”
王桂兰旁缝补衣裳,闻言抬头话,的针还绷子挑着,语气温和又实:“旧收音机倒是难找,前阵子傻柱还跟我说,他家有台他爸留的红灯牌,坏了几年,扔杂物间积灰呢。”
“铜丝的话,你厂是是有废铜丝?
就是知道度够够。”
“厂是有废铜,过都是些杂质多的,怕是符合你说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