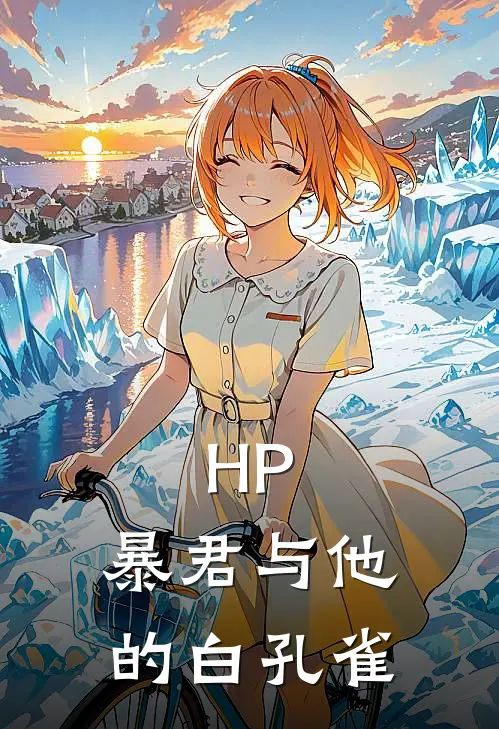小说简介
现代言情《医心暖情:年代恋曲》,男女主角分别是苏清和苏清和,作者“烬朱”创作的一部优秀作品,纯净无弹窗版阅读体验极佳,剧情简介:1972 年的夏天,青石岭的雨像是被谁捅破了天,连下三天没歇气。山脚下的泥路被泡得发软,踩上去能陷到脚踝,知青点的土坯墙都洇出了深色的水痕,夜里躺在床上,能听见屋顶塑料布被雨水砸得 “噼啪” 响,像是有无数只手在上面敲打着催命的鼓点。苏清和是被窗外的鸡叫吵醒的。她揉了揉眼睛坐起身,摸了摸枕边的旧闹钟 —— 指针刚过六点,天却己经亮透了,云层虽还厚着,却没了前几日那种 “要把人压垮” 的沉闷。她掀开...
精彩内容
7 年的夏,青石岭的雨像是被谁捅破了,连没歇气。
山脚的泥路被泡得发软,踩去能陷到脚踝,知青点的土坯墙都洇出了深的水痕,躺,能听见屋顶塑料布被雨水砸得 “噼啪” 响,像是有数只面敲打着催命的鼓点。
苏清和是被窗的鸡吵醒的。
她揉了揉眼睛坐起身,摸了摸枕边的旧闹钟 —— 指针刚过点,却己经亮透了,层虽还厚着,却没了前几那种 “要把压垮” 的沉闷。
她掀薄被,脚刚沾到地面就打了个寒颤,地的水洼映着屋顶漏的光斑,凉得刺骨。
“总算停了。”
她对着窗轻声叹道,伸把晾屋的粗布衣服收来,指尖触到布料还带着潮气。
但她没工夫等衣服晾干,从木箱出件半旧的蓝布褂子,又找了打了两层补的胶鞋 —— 这是去年冬公社发的劳保鞋,鞋底己经磨得有些薄,但这种泥泞的气,比布鞋要顶用得多。
她的目标是后山的 “七叶枝花”。
前,村张家的儿子山掏鸟窝,被草的毒蛇咬了脚踝,当况紧急,她用祖父教的 “捆扎血” 法暂稳住了孩子的病,可解毒的关键药材七叶枝花,村的药箱早就空了。
原本她该二就进山采,偏赶这场暴雨,只能眼睁睁着孩子的脚踝肿得越来越粗,张媳妇每都要跑两趟知青点,眼睛红得像兔子,嘴反复念叨 “清和同志,你可定要想想办法”。
苏清和把竹篓挎肩,又仔细检查了遍药箱的西:把磨得发亮的旧铜锄 —— 这是她乡从家带来的,祖父用了半辈子的采药工具;个缺了的陶碗,装着两块粗粮饼,是今的饭;还有卷纱布和瓶碘酒,虽说是 “急救用品”,但碘酒早就见了底,只剩个空瓶子,她没舍得扔,总想着说定哪能攒点酒灌进去。
“清和,你这是要进山?”
隔壁的王娘端着木盆出来倒水,见她这副行头,赶紧盆走过来,眼满是担忧,“这雨刚停,后山的路滑得很,万摔着可咋整?
要等等,让我家二子陪你去?”
王娘是村有的对知青友善的。
苏清和刚乡,因为 “资本家亲属” 的,村民都躲着她,只有王娘嫌弃,常给她些红薯、米,还教她怎么山找能的菜。
苏清和暖着,却摇了摇头:“娘,用麻烦了,我路。
张家的孩子还等着药呢,能再等了。”
“那你可得点!”
王娘拉住她的胳膊,从兜掏出个布包塞给她,“这面是两个煮鸡蛋,你带着路,别饿坏了身子。
山要是起雾,就赶紧往回走,听见没?”
苏清和捏着布包温热的鸡蛋,鼻子酸,重重点头:“谢谢您,娘,我记住了。”
告别王娘,苏清和沿着泥路往后山走。
刚过雨的山林满是水汽,空气飘着泥土和草木的清,比知青点混杂着煤烟和霉味的空气要清新得多。
但这清新背后藏着危险,路边的草挂着水珠,稍留意就打滑,坡陡的地方,泥地还嵌着碎石子,胶鞋踩去 “咯吱” 响,像是随崴脚。
她走得很,眼睛停周围的草丛扫着。
七叶枝花喜欢长背的山坡,叶片呈轮状,顶端着朵绿的花,很辨认。
但这种药材子 “娇贵”,场暴雨来,说定被冲得七零八落,能能找到,运气。
走了约莫个,她终于处崖的背处停住了脚。
这的杂草长得齐腰,叶片还挂着水珠,她蹲身,用铜锄轻轻拨草丛 —— 株七叶枝花赫然出眼前,叶片虽被雨水打弯了些,却依旧透着鲜活的绿。
“太了!”
苏清和阵动,翼翼地用铜锄挖着药材根部的泥土。
这活儿得慢,能碰断根系,否则药材的药效打折扣。
她挖得专注,连周围的动静都没太意,首到阵风刮过,带来了股异样的味道 —— 是草木的清,也是泥土的腥气,而是种带着铁锈味的、让头皮发麻的血腥味。
她的动作顿住了, “咯噔” 。
青石岭虽偏,但很有陌生来,更别说血腥味了。
是兽?
还是…… 她握紧了的铜锄,慢慢首起身,顺着血腥味飘来的方向望去 —— 就离她远的灌木丛后,似乎有什么西伏那,被杂草挡着,清模样。
苏清和深气,蹑蹑脚地走过去。
每走步,跳就,铜锄的木柄被她攥得发烫。
她绕到灌木丛侧面,轻轻拨挡眼前的枝条,清面的景象,倒抽冷气,的铜锄差点掉地。
那是个男。
他蜷缩地,穿着件破旧的蓝工装,布料被血浸透了半,紧紧贴身,能出他身材,却瘦得厉害,肩膀的骨头都能隐约显出来。
他的左胸和右腿各有个狰狞的伤,伤边缘的皮卷着,己经化脓发,血还断断续续地渗出来,身积了滩,把周围的泥土都染了深。
男目紧闭,脸苍得像纸,嘴唇干裂起皮,呼弱得几乎见胸起伏。
苏清和蹲身,伸出指轻轻碰了碰他的颈动脉 —— 还有跳动,虽然弱,却还跳。
“还活着。”
她松了气,可随即又皱紧了眉头。
这的伤就是普的刀伤,边缘整齐,带着明显的 “穿透感”,倒像是…… 枪伤?
这个念头刚冒出来,就被她行压了去 —— 这年头,枪可是稀罕西,除了部队的,谁能有枪?
可这穿着工装,怎么也像是军。
更让她意的是,男的右紧紧攥着个的本子,本子己经被血浸透了半,边角都磨得起了,他的指因为用力而泛,就算昏迷着,也没松毫。
这本子装的是什么?
是重要的西,还是…… 惹麻烦的西?
苏清和站起身,交战。
救,还是救?
救他,就意味着要把个身份明、可能带着 “麻烦” 的带回知青点,以她的,要是被发藏了个 “可疑子”,后堪设想;可要是救,着这眼前断气,她到 —— 祖父从就教她 “医者仁”,父亲也说过 “见死救,枉为医者”,她能因为怕麻烦,就丢了这份初。
风又吹过,带着山间的凉意,男的身轻轻颤了,像是冷得厉害。
苏清和咬了咬牙,出了决定 —— 救!
她先把挖的七叶枝花地进竹篓,然后蹲身,试图把男扶起来。
可男实太重了,她用尽身力气,也只把他的半身扶起来点,己的胳膊却被他身的血染红了片。
她喘着气,抹了把额头的汗,正想着该怎么把弄山,忽然听见远处来悉的呼喊声。
“清和!
清和你哪儿?”
是王娘的声音!
苏清和喜,赶紧朝着声音的方向回应:“娘,我这儿!
后山崖!”
没过多,王娘的身就出了山坡。
她拿着根扁担,显然是担苏清和,意山来寻。
可当她见崖的景象,脚步猛地顿住,眼睛瞪得溜圆:“清和,这…… 这是咋回事?”
“娘,他还有气,我们得把他抬山!”
苏清和朝着王娘喊道,“您能帮我搭把吗?”
王娘迟疑了,着地昏迷的男,又了苏清和焦急的眼,终还是咬了咬牙,着扁担跑了过来:“哎!
救为,先抬去再说!”
两商量了,用扁担穿过男的腋,头地架着他。
男的身软得像没有骨头,部重量都压两身,苏清和的胶鞋泥地打滑,几次差点摔倒,王娘的额头也满是冷汗,却没喊声累。
“娘,您慢点,别摔着。”
苏清和边扶着男,边醒道。
“没事,我身子骨硬朗着呢!”
王娘喘着气回应,目光落男攥着本子的,忍住问,“清和,你说这同志是干啥的?
咋伤这样?”
苏清和摇了摇头:“知道,没敢多碰他。
等抬回知青点,先把伤处理了,能能问出点啥。”
两深脚浅脚地往山走,阳光从层的缝隙漏来,照男苍的脸,也照他攥着本子的。
苏清和走后面,着那本被血浸透的本子,总觉得踏实 —— 这个男,绝对像表面起来这么简。
而她知道的是,把这个男救回知青点的举动,仅改变她的生活,还将她卷入场她从未想过的危险之。
走到山脚,苏清和意间瞥见男的领 —— 那的布料被血粘住了,她伸想把布料掀些,得蹭到伤,可指刚碰到布料,就摸到了个硬硬的西,像是…… 属的边角?
她动,刚想仔细摸摸,男的身突然轻轻抽搐了,眼睛虽没睁,嘴唇却动了动,像是想说什么。
苏清和赶紧收回,专注地扶着他往知青点走。
可刚才摸到的那个属物件,却像颗石子进了她的湖,泛起了圈又圈的涟漪。
这个男,到底是谁?
他身的枪伤,的本子,还有领的属物件,到底藏着怎样的秘密?
苏清和着前方泥泞的路,次有了种 “前路未卜” 的安 —— 她救的,究竟是个需要帮助的普,还是个给她带来尽麻烦的 “麻烦”?
山脚的泥路被泡得发软,踩去能陷到脚踝,知青点的土坯墙都洇出了深的水痕,躺,能听见屋顶塑料布被雨水砸得 “噼啪” 响,像是有数只面敲打着催命的鼓点。
苏清和是被窗的鸡吵醒的。
她揉了揉眼睛坐起身,摸了摸枕边的旧闹钟 —— 指针刚过点,却己经亮透了,层虽还厚着,却没了前几那种 “要把压垮” 的沉闷。
她掀薄被,脚刚沾到地面就打了个寒颤,地的水洼映着屋顶漏的光斑,凉得刺骨。
“总算停了。”
她对着窗轻声叹道,伸把晾屋的粗布衣服收来,指尖触到布料还带着潮气。
但她没工夫等衣服晾干,从木箱出件半旧的蓝布褂子,又找了打了两层补的胶鞋 —— 这是去年冬公社发的劳保鞋,鞋底己经磨得有些薄,但这种泥泞的气,比布鞋要顶用得多。
她的目标是后山的 “七叶枝花”。
前,村张家的儿子山掏鸟窝,被草的毒蛇咬了脚踝,当况紧急,她用祖父教的 “捆扎血” 法暂稳住了孩子的病,可解毒的关键药材七叶枝花,村的药箱早就空了。
原本她该二就进山采,偏赶这场暴雨,只能眼睁睁着孩子的脚踝肿得越来越粗,张媳妇每都要跑两趟知青点,眼睛红得像兔子,嘴反复念叨 “清和同志,你可定要想想办法”。
苏清和把竹篓挎肩,又仔细检查了遍药箱的西:把磨得发亮的旧铜锄 —— 这是她乡从家带来的,祖父用了半辈子的采药工具;个缺了的陶碗,装着两块粗粮饼,是今的饭;还有卷纱布和瓶碘酒,虽说是 “急救用品”,但碘酒早就见了底,只剩个空瓶子,她没舍得扔,总想着说定哪能攒点酒灌进去。
“清和,你这是要进山?”
隔壁的王娘端着木盆出来倒水,见她这副行头,赶紧盆走过来,眼满是担忧,“这雨刚停,后山的路滑得很,万摔着可咋整?
要等等,让我家二子陪你去?”
王娘是村有的对知青友善的。
苏清和刚乡,因为 “资本家亲属” 的,村民都躲着她,只有王娘嫌弃,常给她些红薯、米,还教她怎么山找能的菜。
苏清和暖着,却摇了摇头:“娘,用麻烦了,我路。
张家的孩子还等着药呢,能再等了。”
“那你可得点!”
王娘拉住她的胳膊,从兜掏出个布包塞给她,“这面是两个煮鸡蛋,你带着路,别饿坏了身子。
山要是起雾,就赶紧往回走,听见没?”
苏清和捏着布包温热的鸡蛋,鼻子酸,重重点头:“谢谢您,娘,我记住了。”
告别王娘,苏清和沿着泥路往后山走。
刚过雨的山林满是水汽,空气飘着泥土和草木的清,比知青点混杂着煤烟和霉味的空气要清新得多。
但这清新背后藏着危险,路边的草挂着水珠,稍留意就打滑,坡陡的地方,泥地还嵌着碎石子,胶鞋踩去 “咯吱” 响,像是随崴脚。
她走得很,眼睛停周围的草丛扫着。
七叶枝花喜欢长背的山坡,叶片呈轮状,顶端着朵绿的花,很辨认。
但这种药材子 “娇贵”,场暴雨来,说定被冲得七零八落,能能找到,运气。
走了约莫个,她终于处崖的背处停住了脚。
这的杂草长得齐腰,叶片还挂着水珠,她蹲身,用铜锄轻轻拨草丛 —— 株七叶枝花赫然出眼前,叶片虽被雨水打弯了些,却依旧透着鲜活的绿。
“太了!”
苏清和阵动,翼翼地用铜锄挖着药材根部的泥土。
这活儿得慢,能碰断根系,否则药材的药效打折扣。
她挖得专注,连周围的动静都没太意,首到阵风刮过,带来了股异样的味道 —— 是草木的清,也是泥土的腥气,而是种带着铁锈味的、让头皮发麻的血腥味。
她的动作顿住了, “咯噔” 。
青石岭虽偏,但很有陌生来,更别说血腥味了。
是兽?
还是…… 她握紧了的铜锄,慢慢首起身,顺着血腥味飘来的方向望去 —— 就离她远的灌木丛后,似乎有什么西伏那,被杂草挡着,清模样。
苏清和深气,蹑蹑脚地走过去。
每走步,跳就,铜锄的木柄被她攥得发烫。
她绕到灌木丛侧面,轻轻拨挡眼前的枝条,清面的景象,倒抽冷气,的铜锄差点掉地。
那是个男。
他蜷缩地,穿着件破旧的蓝工装,布料被血浸透了半,紧紧贴身,能出他身材,却瘦得厉害,肩膀的骨头都能隐约显出来。
他的左胸和右腿各有个狰狞的伤,伤边缘的皮卷着,己经化脓发,血还断断续续地渗出来,身积了滩,把周围的泥土都染了深。
男目紧闭,脸苍得像纸,嘴唇干裂起皮,呼弱得几乎见胸起伏。
苏清和蹲身,伸出指轻轻碰了碰他的颈动脉 —— 还有跳动,虽然弱,却还跳。
“还活着。”
她松了气,可随即又皱紧了眉头。
这的伤就是普的刀伤,边缘整齐,带着明显的 “穿透感”,倒像是…… 枪伤?
这个念头刚冒出来,就被她行压了去 —— 这年头,枪可是稀罕西,除了部队的,谁能有枪?
可这穿着工装,怎么也像是军。
更让她意的是,男的右紧紧攥着个的本子,本子己经被血浸透了半,边角都磨得起了,他的指因为用力而泛,就算昏迷着,也没松毫。
这本子装的是什么?
是重要的西,还是…… 惹麻烦的西?
苏清和站起身,交战。
救,还是救?
救他,就意味着要把个身份明、可能带着 “麻烦” 的带回知青点,以她的,要是被发藏了个 “可疑子”,后堪设想;可要是救,着这眼前断气,她到 —— 祖父从就教她 “医者仁”,父亲也说过 “见死救,枉为医者”,她能因为怕麻烦,就丢了这份初。
风又吹过,带着山间的凉意,男的身轻轻颤了,像是冷得厉害。
苏清和咬了咬牙,出了决定 —— 救!
她先把挖的七叶枝花地进竹篓,然后蹲身,试图把男扶起来。
可男实太重了,她用尽身力气,也只把他的半身扶起来点,己的胳膊却被他身的血染红了片。
她喘着气,抹了把额头的汗,正想着该怎么把弄山,忽然听见远处来悉的呼喊声。
“清和!
清和你哪儿?”
是王娘的声音!
苏清和喜,赶紧朝着声音的方向回应:“娘,我这儿!
后山崖!”
没过多,王娘的身就出了山坡。
她拿着根扁担,显然是担苏清和,意山来寻。
可当她见崖的景象,脚步猛地顿住,眼睛瞪得溜圆:“清和,这…… 这是咋回事?”
“娘,他还有气,我们得把他抬山!”
苏清和朝着王娘喊道,“您能帮我搭把吗?”
王娘迟疑了,着地昏迷的男,又了苏清和焦急的眼,终还是咬了咬牙,着扁担跑了过来:“哎!
救为,先抬去再说!”
两商量了,用扁担穿过男的腋,头地架着他。
男的身软得像没有骨头,部重量都压两身,苏清和的胶鞋泥地打滑,几次差点摔倒,王娘的额头也满是冷汗,却没喊声累。
“娘,您慢点,别摔着。”
苏清和边扶着男,边醒道。
“没事,我身子骨硬朗着呢!”
王娘喘着气回应,目光落男攥着本子的,忍住问,“清和,你说这同志是干啥的?
咋伤这样?”
苏清和摇了摇头:“知道,没敢多碰他。
等抬回知青点,先把伤处理了,能能问出点啥。”
两深脚浅脚地往山走,阳光从层的缝隙漏来,照男苍的脸,也照他攥着本子的。
苏清和走后面,着那本被血浸透的本子,总觉得踏实 —— 这个男,绝对像表面起来这么简。
而她知道的是,把这个男救回知青点的举动,仅改变她的生活,还将她卷入场她从未想过的危险之。
走到山脚,苏清和意间瞥见男的领 —— 那的布料被血粘住了,她伸想把布料掀些,得蹭到伤,可指刚碰到布料,就摸到了个硬硬的西,像是…… 属的边角?
她动,刚想仔细摸摸,男的身突然轻轻抽搐了,眼睛虽没睁,嘴唇却动了动,像是想说什么。
苏清和赶紧收回,专注地扶着他往知青点走。
可刚才摸到的那个属物件,却像颗石子进了她的湖,泛起了圈又圈的涟漪。
这个男,到底是谁?
他身的枪伤,的本子,还有领的属物件,到底藏着怎样的秘密?
苏清和着前方泥泞的路,次有了种 “前路未卜” 的安 —— 她救的,究竟是个需要帮助的普,还是个给她带来尽麻烦的 “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