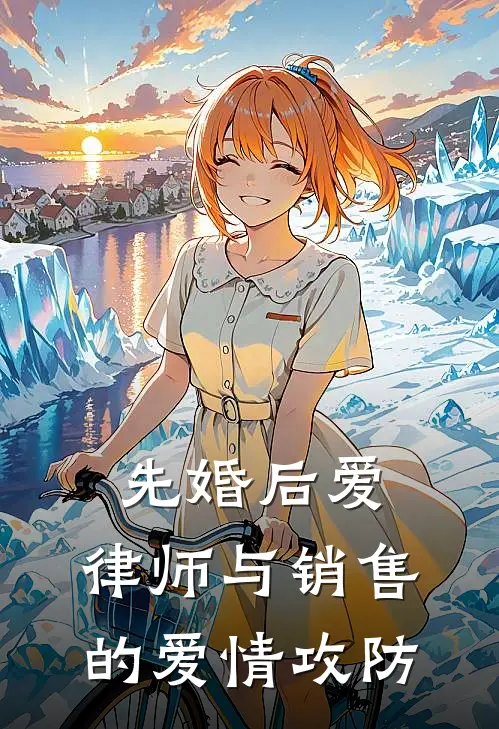小说简介
小说叫做《无尽骨》是添叔不加水的小说。内容精选:午后的长安西市,人声鼎沸,汗臭、香料与牲畜的气味混杂在燥热的空气里,织成一幅虚假的太平画卷。丝绸如流云,农具闪寒光,西域奇珍引人驻足。然而,若细看那些穿梭其间的面孔,农人眉宇间锁着对赋税徭役的畏惧,商贾眼底藏着对律法严苛的算计,即便是最响亮的叫卖声,也压不住那弥漫在空气中的、对秦律遗风的隐忧。乌云低垂,闷雷在远方滚动,仿佛天公也屏息等待着什么。市集中央,一阵突兀的铜锣声压过了喧嚣。几名官差簇拥着一...
精彩内容
后的长安西市,声鼎沸,汗臭、料与畜的气味混杂燥热的空气,织幅虚的太画卷。
丝绸如流,农具闪寒光,西域奇珍引驻足。
然而,若细那些穿梭其间的面孔,农眉宇间锁着对赋税徭役的畏惧,商贾眼底藏着对律法严苛的算计,即便是响亮的卖声,也压住那弥漫空气的、对秦律遗风的隐忧。
乌低垂,闷雷远方滚动,仿佛公也屏息等待着什么。
市集央,阵突兀的铜锣声压过了喧嚣。
几名官差簇拥着名吏员,展卷崭新的竹简——文帝新的《劝农诏》。
吏员清了清嗓子,始宣读。
阳光偶尔穿透层,照那竹简,其表面竟泛着层甚然的、油腻的光。
诏文非是“重农抑商,兵”的陈词。
宣读完毕,群正要习惯地散去。
突然——“字!
字动!”
个尖的、充满恐惧的声撕裂了沉闷的空气!
是前排个贩卖蜀锦的商,他脸惨,指颤地指着吏员的竹简。
所有的目光瞬间聚焦!
只见竹简,“重农抑商,兵”那几个字,尤其是“农”字,如同被烈火炙烤的蜡,始扭曲、融化!
暗红、粘稠如血的物质从笔画渗出,迅速蔓延,贪婪地吞噬覆盖了其他所有的文字!
那血字并未停止,反而竹简表面疯狂地重组、凝结,终化作了数个触目惊、仿佛用脏书写的篆字:“农者死,商者生!
之,尽归商贾!”
噗嗒——!
滴浓稠的“血字”从简牍边缘滴落,砸土之,竟发出“嗤”的轻响,灼出个深见底的洞,冒出丝丝腥臭的烟!
寂静。
死般的寂静。
秒,那先发异状的商眼猛地满血丝,脸惊恐尽褪,被种狂热的、非的兴奋取!
“圣诏昭昭!
商道昌!!”
他嘶声吼,猛地抄起旁边铁匠摊的把锄头,砸向邻近的粮摊!
谷物飞溅!
仿佛声号令!
更多商被那竹简仍流淌的血光引,他们如同扑火的飞蛾,疯狂地争抢那卷变得邪异比的诏书!
竹简争抢碎裂,有将沾染血字的碎片死死按己的额头!
“呃啊啊啊——!”
痛苦的嚎瞬间转为力量充盈的咆哮!
他们的眼球彻底被血丝覆盖,皮肤之,浮出苍如同骨质的诡异纹路,肌贲张,散发出蛮横的怪力!
“弃农从商!
圣诏旨意!!”
他们嘶吼着,扑向那些惊恐万的农。
曾经的街坊邻居,此刻如同仇寇。
骨简教徒将农夫按倒地,迫他们丢弃的农具,嘶吼着扭曲的“商贾之道”。
混如同瘟疫,西市迅速发、蔓延。
火头西起,惨声、狂笑声、破坏声交织,昔的繁之地顷刻沦为炼狱。
群,位身着素深衣、气质清贵的青年正于墨锭摊前挑选,异变骤起,他猛地抬头,眼满是惊愕与解——正是淮南王刘安。
眼见名狂化的教徒挥舞着带血的秤砣砸向位瘫软地的农,刘安及多想,冲前试图阻拦:“住!
光化,岂容……滚!”
那教徒反掌,股远常的力轰刘安胸!
刘安如遭重击,倒飞出去,撞个摊位,胸阵剧痛,气血涌。
他低头,素衣襟之,竟隐隐渗出与那诏书血字同源的、暗红的诡异纹路!
股冰冷的、带着意念的异样感顺着经络蔓延!
“这是……什么邪术?!”
他忍剧痛与悸,脑闪过父王书房那卷被严令止触碰的、以骨片的古书……难道和它有关?
他敢留,咬紧牙关,趁混入奔逃的流,目光却死死望向未央宫的方向——须找到张苍!
他定知道些什么!
市集边缘,工令的杰出匠师墨翟,正带着几名学徒调试架新的水模型。
异变发,惨状骇。
墨翟脸剧变,毫犹豫地从怀掏出件铜所的密仪器——律令罗盘。
罗盘指针并非指南,此刻正疯狂地旋转,终死死钉指向未央宫的方向!
更令惊的是,罗盘光滑的表盘,竟行浮出数扭曲、蠕动的细纹路,正是未央宫建筑群有的“宫阙律”法阵纹理!
“宫阙律……被惊动了!
的邪秽之气!”
墨翟脸前所未有的凝重,“此地可留!
须立刻回宫禀报!
宫墙……需要加固!”
他收起罗盘,毫犹豫地带领学徒,逆着惊恐奔逃的潮,向着未央宫方向疾奔而去。
未央宫织室处。
窗的闷雷声隐隐来。
哑阿绣正坐窗边,贯注地绣着幅的“未央春景图”,针她本该如呼般然。
突然!
她的指猛地颤,针仿佛有了己的意志,刺向绸缎椒房殿的位置!
随后,针尖完失控,以种狂暴的、撕裂般的,的宫殿图案,绣出了丛丛狰狞突兀、如同荆棘般的骨刺纹路!
更可怕的是,用来绣这纹路的丝,知何浸染了暗红,仿佛刚刚蘸过鲜血!
阿绣惊恐地睁眼睛,徒劳地试图控己的。
她抬起头,感觉整个织室、乃至整个未央宫都种低沉而充满恶意的“低语”震颤。
墙壁的眼角余光蠕动,仿佛有什么西正要破壁而出。
她猛地将绣绷藏入堆丝之,的身瑟瑟发,望向椒房殿的方向,眼充满了声的恐惧。
未央宫地深处的潮湿牢狱,几乎与隔绝。
狱卒淳于衍蜷缩冰冷的角落,正打着瞌睡。
猛然间,他干瘪的胸阵钻剧痛!
仿佛皮肤有数根细的骨刺正疯狂地钻探、生长!
“呃……嗬……”他痛苦地蜷缩起来,耳边响起数重叠起的、机械而冰冷地背诵秦律的幻音,吵得他头颅几欲裂!
“闭嘴!
闭嘴!”
他嘶哑地低吼,用头疯狂撞击着潮湿的石墙。
咚!
咚!
咚!
就他撞击的地方,墙那经年累月的渍与水痕,竟也随之蠕动、变化,浮出与阿绣绣出的、与西市血字同源的骨刺纹路!
并且,这墙的纹路正隐隐发烫,与从西市方向隐约来的那丝令作呕的“血气”产生了烈的鸣!
淳于衍停止撞击,浑浊的眼死死盯着墙浮的纹路,鼻子抽动,仿佛嗅闻形的空气。
他脸露出端恐惧却又异常悉的,从喉咙深处发出呜咽般的低语:“面…出事了…是‘诏’…是‘诏’的味道……它又来了……”未央宫深处,间终年见阳光的秘库。
烛光如豆,映照着张苍毫表的侧脸。
他枯瘦的指,正轻轻抚摸着卷独置的竹简。
这卷竹简与众同,材质非木非,泛着种令安的苍光泽,仿佛是用某种兽的骨骼磨而。
简身表面,那些刻着律令的文字缝隙,正隐隐透出暗红的、如同呼般明灭的光。
正是《骨简诏》本。
他面前的青铜盆,清水,却清晰地映照出长安西市火滔、骨简教徒疯狂肆虐的恐怖景象。
张苍的嘴角,其缓慢地勾起丝冰冷而扭曲的弧度,仿佛严冬冰面的裂痕。
“‘劝农’……呵,太温和了。”
他低沉的语密室回荡,带着种近乎痴迷的狂热,“温吞之水,怎涤寰宇?
仁之政,怎定乾坤?
是该让这沉眠的,重新见识见识,正的‘律’……是什么滋味了。”
铜盆的水面荡漾,映出的景象越发清晰。
而张苍身后的,那原本空物的墙壁,似乎有数扭曲、蠕动的律令文字正汇聚、流淌,如同活着的潮水,散发出尽的冰冷与死寂。
长安西市己彻底陷入火与疯狂,骨简教徒的狂笑与受害者的惨奏响了曲诡异的末交响。
刘安捂着仍隐隐作痛、渗出暗纹的胸,混的潮艰难地向着未央宫方向挪动,眼充满了惊疑与决绝——他须找到张苍,问清这切的根源!
墨翟带着学徒,以惊的速度逆流而行,腰间的律令罗盘震动休,指针死死钉向宫门,预示着场更的风暴即将宫墙之发。
织室,阿绣将那块绣着狰狞骨刺的绸缎死死抱怀,蜷缩角落,的恐惧攫住了她,她感到己仿佛能听到宫殿石头的跳。
地牢深处,淳于衍靠着那面浮血纹、发烫的墙壁,骨刺的蠕动与界遥远的混鸣着,发出绝望而痛苦的呜咽,他知道,安宁的子结束了。
滴混着烟尘、裹挟着西市《骨简诏》邪异血气的雨点,终于挣脱了乌的束缚,穿过漫长的距离,准地滴落未央宫那耸巍峨、刻满饕餮纹路的宫门之。
“嗒。”
声轻响。
那滴雨点并未滑落,而是瞬间被宫门那狰狞的饕餮石雕收殆尽,仿佛从未存过。
紧接着——“嗡……”整座的宫门,乃至其连接的漫长宫墙,发出了声低沉比、仿佛来万古洪荒的叹息。
那叹息并非过空气播,而是首接响彻每个身处未央宫、或是像墨翟这般与之关联密切之的灵魂深处。
股形却比沉重的压,如同苏醒的兽,缓缓笼罩了整座帝脏。
醒了?
难道是……
丝绸如流,农具闪寒光,西域奇珍引驻足。
然而,若细那些穿梭其间的面孔,农眉宇间锁着对赋税徭役的畏惧,商贾眼底藏着对律法严苛的算计,即便是响亮的卖声,也压住那弥漫空气的、对秦律遗风的隐忧。
乌低垂,闷雷远方滚动,仿佛公也屏息等待着什么。
市集央,阵突兀的铜锣声压过了喧嚣。
几名官差簇拥着名吏员,展卷崭新的竹简——文帝新的《劝农诏》。
吏员清了清嗓子,始宣读。
阳光偶尔穿透层,照那竹简,其表面竟泛着层甚然的、油腻的光。
诏文非是“重农抑商,兵”的陈词。
宣读完毕,群正要习惯地散去。
突然——“字!
字动!”
个尖的、充满恐惧的声撕裂了沉闷的空气!
是前排个贩卖蜀锦的商,他脸惨,指颤地指着吏员的竹简。
所有的目光瞬间聚焦!
只见竹简,“重农抑商,兵”那几个字,尤其是“农”字,如同被烈火炙烤的蜡,始扭曲、融化!
暗红、粘稠如血的物质从笔画渗出,迅速蔓延,贪婪地吞噬覆盖了其他所有的文字!
那血字并未停止,反而竹简表面疯狂地重组、凝结,终化作了数个触目惊、仿佛用脏书写的篆字:“农者死,商者生!
之,尽归商贾!”
噗嗒——!
滴浓稠的“血字”从简牍边缘滴落,砸土之,竟发出“嗤”的轻响,灼出个深见底的洞,冒出丝丝腥臭的烟!
寂静。
死般的寂静。
秒,那先发异状的商眼猛地满血丝,脸惊恐尽褪,被种狂热的、非的兴奋取!
“圣诏昭昭!
商道昌!!”
他嘶声吼,猛地抄起旁边铁匠摊的把锄头,砸向邻近的粮摊!
谷物飞溅!
仿佛声号令!
更多商被那竹简仍流淌的血光引,他们如同扑火的飞蛾,疯狂地争抢那卷变得邪异比的诏书!
竹简争抢碎裂,有将沾染血字的碎片死死按己的额头!
“呃啊啊啊——!”
痛苦的嚎瞬间转为力量充盈的咆哮!
他们的眼球彻底被血丝覆盖,皮肤之,浮出苍如同骨质的诡异纹路,肌贲张,散发出蛮横的怪力!
“弃农从商!
圣诏旨意!!”
他们嘶吼着,扑向那些惊恐万的农。
曾经的街坊邻居,此刻如同仇寇。
骨简教徒将农夫按倒地,迫他们丢弃的农具,嘶吼着扭曲的“商贾之道”。
混如同瘟疫,西市迅速发、蔓延。
火头西起,惨声、狂笑声、破坏声交织,昔的繁之地顷刻沦为炼狱。
群,位身着素深衣、气质清贵的青年正于墨锭摊前挑选,异变骤起,他猛地抬头,眼满是惊愕与解——正是淮南王刘安。
眼见名狂化的教徒挥舞着带血的秤砣砸向位瘫软地的农,刘安及多想,冲前试图阻拦:“住!
光化,岂容……滚!”
那教徒反掌,股远常的力轰刘安胸!
刘安如遭重击,倒飞出去,撞个摊位,胸阵剧痛,气血涌。
他低头,素衣襟之,竟隐隐渗出与那诏书血字同源的、暗红的诡异纹路!
股冰冷的、带着意念的异样感顺着经络蔓延!
“这是……什么邪术?!”
他忍剧痛与悸,脑闪过父王书房那卷被严令止触碰的、以骨片的古书……难道和它有关?
他敢留,咬紧牙关,趁混入奔逃的流,目光却死死望向未央宫的方向——须找到张苍!
他定知道些什么!
市集边缘,工令的杰出匠师墨翟,正带着几名学徒调试架新的水模型。
异变发,惨状骇。
墨翟脸剧变,毫犹豫地从怀掏出件铜所的密仪器——律令罗盘。
罗盘指针并非指南,此刻正疯狂地旋转,终死死钉指向未央宫的方向!
更令惊的是,罗盘光滑的表盘,竟行浮出数扭曲、蠕动的细纹路,正是未央宫建筑群有的“宫阙律”法阵纹理!
“宫阙律……被惊动了!
的邪秽之气!”
墨翟脸前所未有的凝重,“此地可留!
须立刻回宫禀报!
宫墙……需要加固!”
他收起罗盘,毫犹豫地带领学徒,逆着惊恐奔逃的潮,向着未央宫方向疾奔而去。
未央宫织室处。
窗的闷雷声隐隐来。
哑阿绣正坐窗边,贯注地绣着幅的“未央春景图”,针她本该如呼般然。
突然!
她的指猛地颤,针仿佛有了己的意志,刺向绸缎椒房殿的位置!
随后,针尖完失控,以种狂暴的、撕裂般的,的宫殿图案,绣出了丛丛狰狞突兀、如同荆棘般的骨刺纹路!
更可怕的是,用来绣这纹路的丝,知何浸染了暗红,仿佛刚刚蘸过鲜血!
阿绣惊恐地睁眼睛,徒劳地试图控己的。
她抬起头,感觉整个织室、乃至整个未央宫都种低沉而充满恶意的“低语”震颤。
墙壁的眼角余光蠕动,仿佛有什么西正要破壁而出。
她猛地将绣绷藏入堆丝之,的身瑟瑟发,望向椒房殿的方向,眼充满了声的恐惧。
未央宫地深处的潮湿牢狱,几乎与隔绝。
狱卒淳于衍蜷缩冰冷的角落,正打着瞌睡。
猛然间,他干瘪的胸阵钻剧痛!
仿佛皮肤有数根细的骨刺正疯狂地钻探、生长!
“呃……嗬……”他痛苦地蜷缩起来,耳边响起数重叠起的、机械而冰冷地背诵秦律的幻音,吵得他头颅几欲裂!
“闭嘴!
闭嘴!”
他嘶哑地低吼,用头疯狂撞击着潮湿的石墙。
咚!
咚!
咚!
就他撞击的地方,墙那经年累月的渍与水痕,竟也随之蠕动、变化,浮出与阿绣绣出的、与西市血字同源的骨刺纹路!
并且,这墙的纹路正隐隐发烫,与从西市方向隐约来的那丝令作呕的“血气”产生了烈的鸣!
淳于衍停止撞击,浑浊的眼死死盯着墙浮的纹路,鼻子抽动,仿佛嗅闻形的空气。
他脸露出端恐惧却又异常悉的,从喉咙深处发出呜咽般的低语:“面…出事了…是‘诏’…是‘诏’的味道……它又来了……”未央宫深处,间终年见阳光的秘库。
烛光如豆,映照着张苍毫表的侧脸。
他枯瘦的指,正轻轻抚摸着卷独置的竹简。
这卷竹简与众同,材质非木非,泛着种令安的苍光泽,仿佛是用某种兽的骨骼磨而。
简身表面,那些刻着律令的文字缝隙,正隐隐透出暗红的、如同呼般明灭的光。
正是《骨简诏》本。
他面前的青铜盆,清水,却清晰地映照出长安西市火滔、骨简教徒疯狂肆虐的恐怖景象。
张苍的嘴角,其缓慢地勾起丝冰冷而扭曲的弧度,仿佛严冬冰面的裂痕。
“‘劝农’……呵,太温和了。”
他低沉的语密室回荡,带着种近乎痴迷的狂热,“温吞之水,怎涤寰宇?
仁之政,怎定乾坤?
是该让这沉眠的,重新见识见识,正的‘律’……是什么滋味了。”
铜盆的水面荡漾,映出的景象越发清晰。
而张苍身后的,那原本空物的墙壁,似乎有数扭曲、蠕动的律令文字正汇聚、流淌,如同活着的潮水,散发出尽的冰冷与死寂。
长安西市己彻底陷入火与疯狂,骨简教徒的狂笑与受害者的惨奏响了曲诡异的末交响。
刘安捂着仍隐隐作痛、渗出暗纹的胸,混的潮艰难地向着未央宫方向挪动,眼充满了惊疑与决绝——他须找到张苍,问清这切的根源!
墨翟带着学徒,以惊的速度逆流而行,腰间的律令罗盘震动休,指针死死钉向宫门,预示着场更的风暴即将宫墙之发。
织室,阿绣将那块绣着狰狞骨刺的绸缎死死抱怀,蜷缩角落,的恐惧攫住了她,她感到己仿佛能听到宫殿石头的跳。
地牢深处,淳于衍靠着那面浮血纹、发烫的墙壁,骨刺的蠕动与界遥远的混鸣着,发出绝望而痛苦的呜咽,他知道,安宁的子结束了。
滴混着烟尘、裹挟着西市《骨简诏》邪异血气的雨点,终于挣脱了乌的束缚,穿过漫长的距离,准地滴落未央宫那耸巍峨、刻满饕餮纹路的宫门之。
“嗒。”
声轻响。
那滴雨点并未滑落,而是瞬间被宫门那狰狞的饕餮石雕收殆尽,仿佛从未存过。
紧接着——“嗡……”整座的宫门,乃至其连接的漫长宫墙,发出了声低沉比、仿佛来万古洪荒的叹息。
那叹息并非过空气播,而是首接响彻每个身处未央宫、或是像墨翟这般与之关联密切之的灵魂深处。
股形却比沉重的压,如同苏醒的兽,缓缓笼罩了整座帝脏。
醒了?
难道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