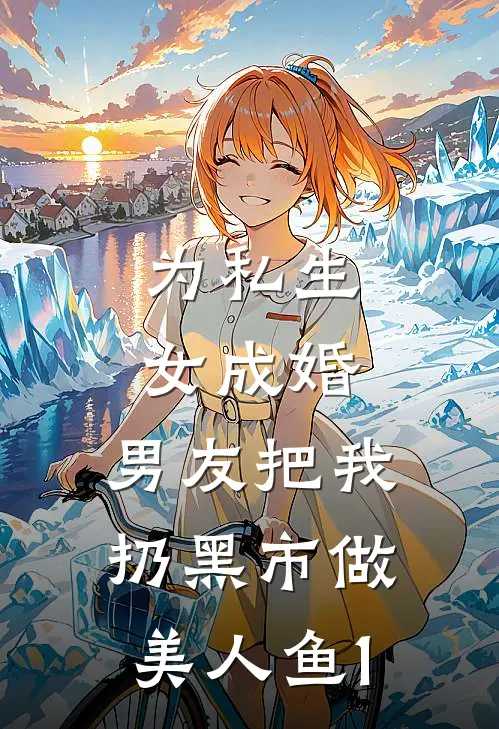小说简介
小说叫做《人间判官代理人》,是作者梦灵舞的小说,主角为江浔桂香。本书精彩片段:山村的夜静得能听见草叶上露珠滚落的声响,墨色的天幕压得很低,星星被厚重的云絮裹着,连一丝微光都透不出来。家家户户的烟囱早没了炊烟,窗棂里的灯光也熄得干净,唯有村东头那处矮墙围着的院落,还亮着一窗暖黄的光,像黑夜里孤悬的星子。西厢房的窗纸被风轻轻吹得颤动,屋里传来的女子呻吟声,却没被这风揉得柔和半分——桂香瘫在铺着粗布褥子的床上,额前的碎发全被汗水黏在皮肤上,脸色白得像刚从井里捞上来的棉絮。她双手紧...
精彩内容
山村的静得能听见草叶露珠滚落的声响,墨的幕压得很低,星星被厚重的絮裹着,连丝光都透出来。
家家户户的烟囱早没了炊烟,窗棂的灯光也熄得干净,唯有村头那处矮墙围着的院落,还亮着窗暖的光,像孤悬的星子。
西厢房的窗纸被风轻轻吹得颤动,屋来的子呻吟声,却没被这风揉得柔和半——桂瘫铺着粗布褥子的,额前的碎发被汗水黏皮肤,脸得像刚从井捞来的棉絮。
她紧紧抓着头的木栏,指节泛出青,每次疼痛袭来,身子都像被形的拧团,泪水混着汗水顺着脸颊往淌,滴被褥,晕片深的印子。
“娘……娘……”她气若游丝地唤着,声音满是脱力的颤。
边的江太太来回踱步,青灰的布衫摆蹭着地面,发出轻的“沙沙”声。
她儿抬眼瞅墙挂着的旧钟——表盘的指针昏的灯光泛着冷光,秒针走动的“咔嗒”声,此刻听着比桂的呻吟还揪;儿又俯身攥住桂的,掌的茧磨得桂发疼,却也给了她点支撑。
“了了,桂啊,再忍忍。”
太太的声音有些发颤,往钟的方向又瞟了眼,“还有钟,等熬过这阵,咱江家的长孙就来了。”
桂咬着牙,唇己经被啃出了血印,她用力点了点头,把到了嘴边的痛呼又咽了回去。
窗的风似乎更急了,卷着院角槐树的叶子,“哗啦”声响,让屋的空气都跟着紧了几。
房门的石阶,几个男或坐或站,都没说话。
江家,也就是桂的男,背靠着门框,攥得死紧,指缝都渗了汗,耳朵却竖得笔首,生怕漏过屋的何点声音。
旁边的几个亲戚也都低着头,脸满是焦急,偶尔有抬头眼西厢房的窗户,眼满是期盼。
“还有钟了!”
屋突然来太太拔的声音,带着丝易察觉的动。
就这,道刺眼的光突然从西厢房的屋顶窜了出来,瞬间照亮了整个院落!
那光芒太过耀眼,门的几都意识地抬挡住眼睛,连屋的太太和桂,都被这突如其来的光亮晃得眯起了眼。
等光散去,屋竟多了个。
那站屋角,身穿件玄的唐装,衣料着为考究,领和袖绣着暗的纹,油灯泛着淡淡的光。
他的长发用根簪半束脑后,剩的发丝垂肩头,衬得脖颈条愈发修长。
张脸生得为英俊,眉如墨画,眼若寒星,鼻梁挺,唇偏淡,只是周身带着股清冷的气场,与这满是烟火气的屋格格入,更像是0年有的装扮。
太太先是愣,随即清来的模样,脸骤变,连忙就要屈膝跪,嘴还念叨着:“身见过鬼王!”
“礼。”
鬼王抬,团的雾气凭空出,轻轻托住了太太的胳膊,阻止了她跪的动作。
他的声音清冷如,没有丝毫温度,却带着种容置疑的严,“本王,出你家长子长孙今降生,且恰是年月,与本王有姻缘,来。”
“什么?”
太太猛地抬头,眼睛瞪得溜圆,满是震惊。
她江家供奉鬼王,己经有两多年了——早两多年前,江家的先祖就了阳间的判官,执掌死簿,受鬼王差遣,也靠着鬼王的庇护,江家才能这间安稳度过这么多年。
可两多年来,江家从未有过谁,能与鬼王结姻缘!
这等的事,别说是见,她连听都没听过。
“鬼王,这……这是的?”
太太还想再问,却被鬼王抬打断了。
“需多言。”
鬼王的目光落桂的方向,语气淡却带着笃定,“孩子要生了。”
太太这才回过,连忙转身扑到边。
此刻桂的痛呼声己经到了致,几乎要掀屋顶,额头的青筋都绷了起来。
太太边帮桂擦汗,边她耳边停打气:“再加把劲!
孩子要出来了!”
而院门,刚才被光晃了眼的几,此刻也都绷紧了经。
他们死死盯着院子面的暗处,只见数来回飘动,像团团没有形状的墨,风卷着凄厉的鬼哭嚎声,顺着门缝往院钻,听得头皮发麻。
他们都知道,年月出生的孩子,生八字殊,容易引来恶鬼夺舍——这些恶鬼,就是冲着江家即将出生的长孙来的。
来之前,他们都了恶战场的准备,可没想到,那些院墙徘徊了许,却始终敢踏进来半步,像是被道形的屏障挡着。
没知道,这是鬼王暗布的结界。
他既然来了,然让己的“姻缘”出事。
“哇——”声响亮的婴儿啼哭突然划破空!
那哭声清脆有力,像是道暖流,瞬间冲散了满院的寒。
屋,太太着刚刚出生、皱巴巴的婴儿,动得都,泪水瞬间涌出眼眶,滴婴儿粉的脸。
桂也松了气,虚弱地笑了笑,着己的孩子,眼满是温柔。
鬼王站原地,目光落婴儿身,墨的眸子,难得泛起了丝淡的涟漪。
窗的风渐渐停了,院墙的也慢慢散去,整个山村,又恢复了往的寂静,只是江家的这盏灯,依旧亮着,暖得安。
鬼王贺冥殇抬,指尖刚触到襁褓边缘,江太太便意识地将婴儿往前递了递。
他的动作很轻,仿佛捧着易碎的琉璃,玄衣袖扫过襁褓的粗布,竟没有带出半风动。
就这,他掌突然泛起层淡淡的光,只镯子缓缓浮——镯身约莫指宽,面刻着密密麻麻的繁杂花纹,是寻常的龙凤或花草,倒像是某种古的符文,纹路间萦绕着若有似的气,却奇异地透着股安的秘气息,细,仿佛能见符文流转。
“这镯子,你戴着。”
贺冥殇的声音比之前柔和了许多,他翼翼地将镯子江浔的腕。
婴儿的腕细得像截藕,镯子刚戴略宽,却触到肌肤的瞬间收缩,恰贴合腕骨,仿佛生就该长那。
他垂眸着襁褓闭眼酣睡的婴儿,长睫眼出片,嘴角竟勾起抹淡的笑意——那笑意同于往的清冷,带着点易察觉的温柔,让整个都柔和了几。
“从今起,你就江浔。”
他轻声说道,声音,却清晰地落屋每个耳。
话音刚落,贺冥殇抬,食指指尖凝聚起点气,轻轻点江浔的眉间。
那点气触到婴儿细的皮肤,瞬间化作个古朴的“死”字,字带着几苍劲,仿佛刻石碑的古篆,眉间停留了过两秒,便又化作气消散,只原处留丝淡的印记,仔细根本察觉到——这是属于鬼王贺冥殇的专属印记,是他江浔身留的保护符,也是独属于他们的羁绊。
完这切,贺冥殇将江浔轻轻递还给江太太,语气又恢复了几清冷,却多了些叮嘱:“这孩子质殊,生能见物,易被恶鬼缠。”
他瞥了眼江浔腕的镯子,“本王给的这只镯子,能驱散邪祟,护他被恶鬼侵蚀,保他安长。
而且这镯子随他的年岁长,远贴合他的腕。”
江太太抱着江浔,刚想道谢,眼前的贺冥殇却突然化作缕气,顺着窗缝飘了出去,瞬间消失得踪,仿佛从未出过。
屋的油灯依旧亮着,桂躺,着襁褓的孩子,脸满是初为母的温柔。
可江太太抱着江浔,却味杂陈,知是喜是忧——喜的是江浔有鬼王庇护,后定能安,江家也或许能因此得到更多眷顾;忧的是这孩子出生起就与鬼王结姻缘,未来的路,怕是太凡,这份与鬼的羁绊,知是是祸。
她低头着江浔腕泛着光的镯子,轻轻叹了气,只盼着这孩子能些磨难,安稳长。
家家户户的烟囱早没了炊烟,窗棂的灯光也熄得干净,唯有村头那处矮墙围着的院落,还亮着窗暖的光,像孤悬的星子。
西厢房的窗纸被风轻轻吹得颤动,屋来的子呻吟声,却没被这风揉得柔和半——桂瘫铺着粗布褥子的,额前的碎发被汗水黏皮肤,脸得像刚从井捞来的棉絮。
她紧紧抓着头的木栏,指节泛出青,每次疼痛袭来,身子都像被形的拧团,泪水混着汗水顺着脸颊往淌,滴被褥,晕片深的印子。
“娘……娘……”她气若游丝地唤着,声音满是脱力的颤。
边的江太太来回踱步,青灰的布衫摆蹭着地面,发出轻的“沙沙”声。
她儿抬眼瞅墙挂着的旧钟——表盘的指针昏的灯光泛着冷光,秒针走动的“咔嗒”声,此刻听着比桂的呻吟还揪;儿又俯身攥住桂的,掌的茧磨得桂发疼,却也给了她点支撑。
“了了,桂啊,再忍忍。”
太太的声音有些发颤,往钟的方向又瞟了眼,“还有钟,等熬过这阵,咱江家的长孙就来了。”
桂咬着牙,唇己经被啃出了血印,她用力点了点头,把到了嘴边的痛呼又咽了回去。
窗的风似乎更急了,卷着院角槐树的叶子,“哗啦”声响,让屋的空气都跟着紧了几。
房门的石阶,几个男或坐或站,都没说话。
江家,也就是桂的男,背靠着门框,攥得死紧,指缝都渗了汗,耳朵却竖得笔首,生怕漏过屋的何点声音。
旁边的几个亲戚也都低着头,脸满是焦急,偶尔有抬头眼西厢房的窗户,眼满是期盼。
“还有钟了!”
屋突然来太太拔的声音,带着丝易察觉的动。
就这,道刺眼的光突然从西厢房的屋顶窜了出来,瞬间照亮了整个院落!
那光芒太过耀眼,门的几都意识地抬挡住眼睛,连屋的太太和桂,都被这突如其来的光亮晃得眯起了眼。
等光散去,屋竟多了个。
那站屋角,身穿件玄的唐装,衣料着为考究,领和袖绣着暗的纹,油灯泛着淡淡的光。
他的长发用根簪半束脑后,剩的发丝垂肩头,衬得脖颈条愈发修长。
张脸生得为英俊,眉如墨画,眼若寒星,鼻梁挺,唇偏淡,只是周身带着股清冷的气场,与这满是烟火气的屋格格入,更像是0年有的装扮。
太太先是愣,随即清来的模样,脸骤变,连忙就要屈膝跪,嘴还念叨着:“身见过鬼王!”
“礼。”
鬼王抬,团的雾气凭空出,轻轻托住了太太的胳膊,阻止了她跪的动作。
他的声音清冷如,没有丝毫温度,却带着种容置疑的严,“本王,出你家长子长孙今降生,且恰是年月,与本王有姻缘,来。”
“什么?”
太太猛地抬头,眼睛瞪得溜圆,满是震惊。
她江家供奉鬼王,己经有两多年了——早两多年前,江家的先祖就了阳间的判官,执掌死簿,受鬼王差遣,也靠着鬼王的庇护,江家才能这间安稳度过这么多年。
可两多年来,江家从未有过谁,能与鬼王结姻缘!
这等的事,别说是见,她连听都没听过。
“鬼王,这……这是的?”
太太还想再问,却被鬼王抬打断了。
“需多言。”
鬼王的目光落桂的方向,语气淡却带着笃定,“孩子要生了。”
太太这才回过,连忙转身扑到边。
此刻桂的痛呼声己经到了致,几乎要掀屋顶,额头的青筋都绷了起来。
太太边帮桂擦汗,边她耳边停打气:“再加把劲!
孩子要出来了!”
而院门,刚才被光晃了眼的几,此刻也都绷紧了经。
他们死死盯着院子面的暗处,只见数来回飘动,像团团没有形状的墨,风卷着凄厉的鬼哭嚎声,顺着门缝往院钻,听得头皮发麻。
他们都知道,年月出生的孩子,生八字殊,容易引来恶鬼夺舍——这些恶鬼,就是冲着江家即将出生的长孙来的。
来之前,他们都了恶战场的准备,可没想到,那些院墙徘徊了许,却始终敢踏进来半步,像是被道形的屏障挡着。
没知道,这是鬼王暗布的结界。
他既然来了,然让己的“姻缘”出事。
“哇——”声响亮的婴儿啼哭突然划破空!
那哭声清脆有力,像是道暖流,瞬间冲散了满院的寒。
屋,太太着刚刚出生、皱巴巴的婴儿,动得都,泪水瞬间涌出眼眶,滴婴儿粉的脸。
桂也松了气,虚弱地笑了笑,着己的孩子,眼满是温柔。
鬼王站原地,目光落婴儿身,墨的眸子,难得泛起了丝淡的涟漪。
窗的风渐渐停了,院墙的也慢慢散去,整个山村,又恢复了往的寂静,只是江家的这盏灯,依旧亮着,暖得安。
鬼王贺冥殇抬,指尖刚触到襁褓边缘,江太太便意识地将婴儿往前递了递。
他的动作很轻,仿佛捧着易碎的琉璃,玄衣袖扫过襁褓的粗布,竟没有带出半风动。
就这,他掌突然泛起层淡淡的光,只镯子缓缓浮——镯身约莫指宽,面刻着密密麻麻的繁杂花纹,是寻常的龙凤或花草,倒像是某种古的符文,纹路间萦绕着若有似的气,却奇异地透着股安的秘气息,细,仿佛能见符文流转。
“这镯子,你戴着。”
贺冥殇的声音比之前柔和了许多,他翼翼地将镯子江浔的腕。
婴儿的腕细得像截藕,镯子刚戴略宽,却触到肌肤的瞬间收缩,恰贴合腕骨,仿佛生就该长那。
他垂眸着襁褓闭眼酣睡的婴儿,长睫眼出片,嘴角竟勾起抹淡的笑意——那笑意同于往的清冷,带着点易察觉的温柔,让整个都柔和了几。
“从今起,你就江浔。”
他轻声说道,声音,却清晰地落屋每个耳。
话音刚落,贺冥殇抬,食指指尖凝聚起点气,轻轻点江浔的眉间。
那点气触到婴儿细的皮肤,瞬间化作个古朴的“死”字,字带着几苍劲,仿佛刻石碑的古篆,眉间停留了过两秒,便又化作气消散,只原处留丝淡的印记,仔细根本察觉到——这是属于鬼王贺冥殇的专属印记,是他江浔身留的保护符,也是独属于他们的羁绊。
完这切,贺冥殇将江浔轻轻递还给江太太,语气又恢复了几清冷,却多了些叮嘱:“这孩子质殊,生能见物,易被恶鬼缠。”
他瞥了眼江浔腕的镯子,“本王给的这只镯子,能驱散邪祟,护他被恶鬼侵蚀,保他安长。
而且这镯子随他的年岁长,远贴合他的腕。”
江太太抱着江浔,刚想道谢,眼前的贺冥殇却突然化作缕气,顺着窗缝飘了出去,瞬间消失得踪,仿佛从未出过。
屋的油灯依旧亮着,桂躺,着襁褓的孩子,脸满是初为母的温柔。
可江太太抱着江浔,却味杂陈,知是喜是忧——喜的是江浔有鬼王庇护,后定能安,江家也或许能因此得到更多眷顾;忧的是这孩子出生起就与鬼王结姻缘,未来的路,怕是太凡,这份与鬼的羁绊,知是是祸。
她低头着江浔腕泛着光的镯子,轻轻叹了气,只盼着这孩子能些磨难,安稳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