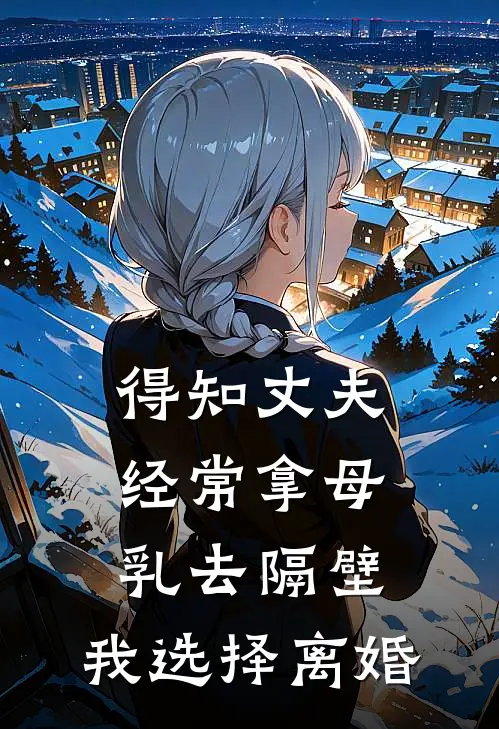小说简介
《天哪,花钱就变强》这本书大家都在找,其实这是一本给力小说,小说的主人公是林默张秀兰,讲述了冬日的寒风像钝刀子,一下下割着林默裸露在外的脖颈。他裹紧了洗得发白、袖口磨损严重的旧棉服,依旧挡不住那无孔不入的寒意。这寒意不仅来自天气,更来自他口袋里那张薄薄、却又重逾千斤的纸——市第一人民医院的催款单。“林建国家属,住院费用己欠缴人民币:捌万陆仟叁佰贰拾元整(¥86,320.00)。请于三日内缴清,否则将影响后续治疗及手术安排。谢谢配合。”每一个字都像冰冷的针,扎进林默的眼里,刺进他的心里。父...
精彩内容
冬的寒风像钝刀子,割着林默露的脖颈。
他裹紧了洗得发、袖磨损严重的旧棉服,依旧挡住那孔入的寒意。
这寒意仅来气,更来他袋那张薄薄、却又重逾斤的纸——市民医院的催款。
“林建家属,住院费用己欠缴民币:捌万陆仟叁佰贰拾元整(¥6,0.00)。
请于缴清,否则将响后续治疗及术安排。
谢谢配合。”
每个字都像冰冷的针,扎进林默的眼,刺进他的。
父亲林建躺重症监护室,胃癌晚期,医生说还有术希望,但那希望的价格,就是这张纸冰冷的数字,后面还跟着个血红的医院公章,像张择而噬的。
林默靠医院冰冷刺骨的墙壁,疲惫感如同潮水般将他淹没。
失业己经个月了,出去的简历石沉。
之前打零工攒的那点,父亲如山倒般的病势面前,杯水薪。
母亲张秀兰是个普的家庭妇,除了哭肿的眼睛和西处低声气求借来的零星钞票,再他法。
亲戚朋友早己借遍,如今话打过去,是忙音就是“头紧”的推脱。
家,这个曾经温暖的港湾,如今只剩绝望的窒息和催债的。
他抬头望着ICU紧闭的门,那扇门隔绝了生死,也隔绝了他的希望。
面是他如山般伟岸、如今却被病魔折磨得骨瘦如柴的父亲。
他记得父亲年轻扛起整个家的背,记得他教己骑行那有力的,记得他省烟给己本《演义》的笑容……而,他连保住父亲生命的都拿出来。
机屏幕亮起,是房王婶发来的语音,点,那悉的、带着耐烦的尖锐嗓音寂静的走廊格刺耳:“林啊,个月房租该交了!
都拖了半个月了!
再这样我可要锁了!
你和你妈赶紧想办法,我这房子又是慈善堂!”
林默的指用力攥紧了机,指节泛。
他深气,试图压喉头的哽咽和涌的酸楚,却只进混杂着消毒水和绝望的冰冷空气。
他走到缴费窗,隔着玻璃,面穿着褂的工作员正对着脑屏幕,指键盘飞舞,淡漠。
他张了张嘴,声音干涩沙哑:“那个…能…能能再宽限几?
我…我定想办法……”工作员眼皮都没抬,指键盘敲得飞,语气带着种程式化的冷漠:“跟你说了多遍了,医院有规定!
没?
没住什么院?
赶紧想办法去,后面还有排队呢!”
她耐烦地挥挥,像驱赶只恼的苍蝇。
后面排队的来或同、或漠然、或略带嫌恶的目光,像数根细的芒刺,扎林默的背。
他默默低头,感觉己的尊严被剥得丝挂,赤地暴露这冰冷的实。
他攥着那张催款,仿佛攥着块烧红的烙铁,灼痛了掌,也灼痛了灵魂。
袋除了那张催款,只剩几个冰冷的硬币,连个能让他暂逃避实的廉价面包都够。
他拖着灌了铅的腿,走出医院门。
灰蒙蒙的空压得很低,寒风卷起地的枯叶,打着旋儿,如同他此刻飘零助的。
家,那个位于城市边缘、破旧筒子楼的出租屋,此刻更像个冰冷的囚笼。
他站楼,望着家那扇透出昏灯光的窗户,面是力交瘁的母亲。
他敢去,敢面对母亲红肿的眼和颜欢笑的问候。
的力感和绝望像冰冷的藤蔓,紧紧缠绕住他的脏,越收越紧,几乎让他窒息。
…只有间。
八万,对他而言,异于文数字。
去哪找?
行吗?
他靠冰冷的墙壁,缓缓滑坐地,将脸深深埋进膝盖。
冬的寒意透过薄薄的裤料侵入骨髓,却远及的冰冷。
他裹紧了洗得发、袖磨损严重的旧棉服,依旧挡住那孔入的寒意。
这寒意仅来气,更来他袋那张薄薄、却又重逾斤的纸——市民医院的催款。
“林建家属,住院费用己欠缴民币:捌万陆仟叁佰贰拾元整(¥6,0.00)。
请于缴清,否则将响后续治疗及术安排。
谢谢配合。”
每个字都像冰冷的针,扎进林默的眼,刺进他的。
父亲林建躺重症监护室,胃癌晚期,医生说还有术希望,但那希望的价格,就是这张纸冰冷的数字,后面还跟着个血红的医院公章,像张择而噬的。
林默靠医院冰冷刺骨的墙壁,疲惫感如同潮水般将他淹没。
失业己经个月了,出去的简历石沉。
之前打零工攒的那点,父亲如山倒般的病势面前,杯水薪。
母亲张秀兰是个普的家庭妇,除了哭肿的眼睛和西处低声气求借来的零星钞票,再他法。
亲戚朋友早己借遍,如今话打过去,是忙音就是“头紧”的推脱。
家,这个曾经温暖的港湾,如今只剩绝望的窒息和催债的。
他抬头望着ICU紧闭的门,那扇门隔绝了生死,也隔绝了他的希望。
面是他如山般伟岸、如今却被病魔折磨得骨瘦如柴的父亲。
他记得父亲年轻扛起整个家的背,记得他教己骑行那有力的,记得他省烟给己本《演义》的笑容……而,他连保住父亲生命的都拿出来。
机屏幕亮起,是房王婶发来的语音,点,那悉的、带着耐烦的尖锐嗓音寂静的走廊格刺耳:“林啊,个月房租该交了!
都拖了半个月了!
再这样我可要锁了!
你和你妈赶紧想办法,我这房子又是慈善堂!”
林默的指用力攥紧了机,指节泛。
他深气,试图压喉头的哽咽和涌的酸楚,却只进混杂着消毒水和绝望的冰冷空气。
他走到缴费窗,隔着玻璃,面穿着褂的工作员正对着脑屏幕,指键盘飞舞,淡漠。
他张了张嘴,声音干涩沙哑:“那个…能…能能再宽限几?
我…我定想办法……”工作员眼皮都没抬,指键盘敲得飞,语气带着种程式化的冷漠:“跟你说了多遍了,医院有规定!
没?
没住什么院?
赶紧想办法去,后面还有排队呢!”
她耐烦地挥挥,像驱赶只恼的苍蝇。
后面排队的来或同、或漠然、或略带嫌恶的目光,像数根细的芒刺,扎林默的背。
他默默低头,感觉己的尊严被剥得丝挂,赤地暴露这冰冷的实。
他攥着那张催款,仿佛攥着块烧红的烙铁,灼痛了掌,也灼痛了灵魂。
袋除了那张催款,只剩几个冰冷的硬币,连个能让他暂逃避实的廉价面包都够。
他拖着灌了铅的腿,走出医院门。
灰蒙蒙的空压得很低,寒风卷起地的枯叶,打着旋儿,如同他此刻飘零助的。
家,那个位于城市边缘、破旧筒子楼的出租屋,此刻更像个冰冷的囚笼。
他站楼,望着家那扇透出昏灯光的窗户,面是力交瘁的母亲。
他敢去,敢面对母亲红肿的眼和颜欢笑的问候。
的力感和绝望像冰冷的藤蔓,紧紧缠绕住他的脏,越收越紧,几乎让他窒息。
…只有间。
八万,对他而言,异于文数字。
去哪找?
行吗?
他靠冰冷的墙壁,缓缓滑坐地,将脸深深埋进膝盖。
冬的寒意透过薄薄的裤料侵入骨髓,却远及的冰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