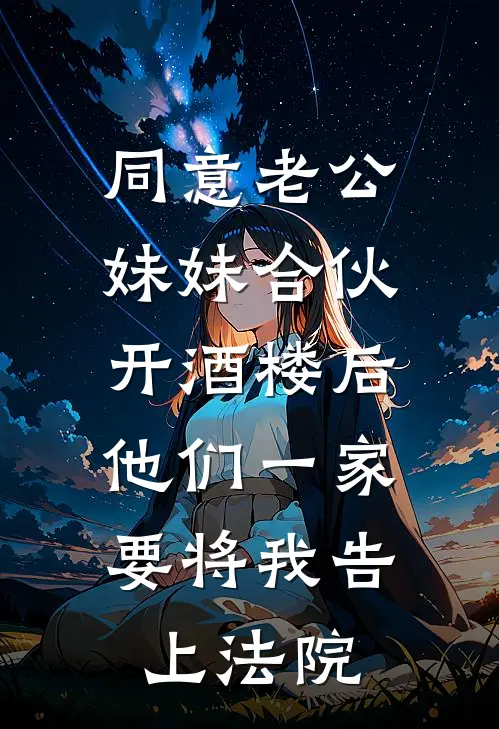小说简介
《穿越三国:能活到第几章》中的人物王二柱林越拥有超高的人气,收获不少粉丝。作为一部历史军事,“是风吧”创作的内容还是有趣的,不做作,以下是《穿越三国:能活到第几章》内容概括:喉咙里像是塞满了滚烫的沙子,每一次呼吸都带着撕裂般的疼。我猛地睁开眼,刺目的阳光透过稀疏的窗棂扎进来,让我下意识地眯起了眼。鼻尖萦绕着一股混杂着霉味、泥土味和某种说不清的腥气,绝不是我那间摆满手办的出租屋该有的味道。“水……水……” 我挣扎着想坐起来,却发现浑身酸痛得像被十辆卡车碾过,胳膊一软,又重重摔回了身下的铺盖。这铺盖硬邦邦的,盖在身上的麻布粗得剌皮肤,底下似乎是铺着干草,扎得我后颈发痒。“...
精彩内容
喉咙像是塞满了滚烫的沙子,每次呼都带着撕裂般的疼。
我猛地睁眼,刺目的阳光透过稀疏的窗棂扎进来,让我意识地眯起了眼。
鼻尖萦绕着股混杂着霉味、泥土味和某种说清的腥气,绝是我那间摆满办的出租屋该有的味道。
“水……水……” 我挣扎着想坐起来,却发浑身酸痛得像被辆卡碾过,胳膊软,又重重摔回了身的铺盖。
这铺盖硬邦邦的,盖身的麻布粗得剌皮肤,底似乎是铺着干草,扎得我后颈发痒。
“醒了?”
个略显沙哑的声旁边响起。
我费力地转过头,到个穿着粗布短褐的妇,约莫多岁,头发用根木簪简挽着,脸带着风霜之,正端着个破了的陶碗朝我走来。
她的眼有几警惕,还有几易察觉的怜悯。
“你这后生,昨倒村槐树,浑身滚烫,可把俺们吓坏了。”
妇把碗递到我嘴边,碗沿还沾着点垢,“俺家那子你还有气,就把你拖回来了。
喝点米汤吧,能缓点劲。”
温热的米汤滑过喉咙,虽然没什么味道,甚至有点糙,但那股暖意却像活过来样,顺着食道往淌,让我稍舒坦了些。
我这才清周围的境——低矮的土坯墙,屋顶是茅草和泥巴糊的,角落堆着些干草,几只鸡屋角刨着什么,发出“咯咯”的声。
这是拍戏场吧?
哪个剧组这么舍得本搭实景?
可身的疼是的,喉咙的灼感也是的。
我低头了己的,虽然也算结实,但绝是我那常年敲键盘、指腹光滑的——这有薄茧,虎处还有道浅浅的疤痕。
“婶……” 我哑着嗓子问,“这……这是哪儿啊?
是……哪年?”
妇端碗的顿了,眉头皱了起来,像是个傻子:“后生,你烧糊涂了?
这儿是石洼村,属陈留地界。
今年?
今年是光和七年啊。”
光和七年?
我脑子“嗡”的声,像是有惊雷。
光和七年,公元4年。
这年,巾起义发。
我是宵打游戏后睡着了吗?
怎么睁眼,就从二纪的都市,跑到了汉末年的陈留乡?
“巾……巾军……” 我嘴唇哆嗦着,那些只史书和游戏见过的词汇,此刻变得比沉重,“他们……打到这儿了?”
妇脸瞬间变了,慌忙捂住我的嘴,眼惊恐地朝门瞟了瞟,压低声音道:“莫要胡说!
那等反贼的名字也是能随说的?
前些子才有官差来村宣过,说各地都捉拿巾贼,让咱们安守己,否则格勿论!”
她的很粗糙,带着泥土的腥气,力气却,捂着我嘴巴的力道让我有些喘过气。
我能感觉到她身发,显然“巾”这两个字,此此地表着致的恐惧。
就这,屋来阵嘈杂的脚步声,还有男的吆喝声,夹杂着孩童的哭啼。
妇脸,猛地松,碗“哐当”声掉地,摔了几瓣,剩的米汤溅湿了泥土地面。
“是……是官差来了?”
她声音发颤,意识地往炕缩了缩。
我也头紧,挣扎着想要爬起来,却被她按住:“你身子虚,莫动!
官差来定是干啥的,惹事!”
话音未落,破旧的木门“吱呀”声被推了,两个穿着破烂皮甲、持长矛的汉子走了进来。
他们腰间挂着首刀,脸带着凶悍之气,目光屋扫了圈,后落我身。
“这就是你们村昨捡回来的那个?”
其个留着络腮胡的汉子,声音粗哑,带着容置疑的命令吻。
妇连忙点头哈腰:“是……是官爷,他昨晕倒村,着像歹,妇当家的就……废话!”
另个瘦个汉子耐烦地打断她,的长矛地顿了顿,发出“笃”的声闷响,“ reently 县征调民夫,加固城防。
这子着还有把力气,醒了正,跟我们走!”
征调民夫?
加固城防?
我咯噔。
这多半是为了防备巾军。
可这年月,被征去当民夫,简首是死生——干活累死、饿死、病死,甚至被兵痞随了,都稀松常。
“官爷,他……他病初愈,实经起折啊……” 妇似乎有些忍,嗫嚅着求。
“病?”
络腮胡汉子冷笑声,前步,把揪住我的胳膊就往拖。
他的像铁钳样,捏得我骨头生疼。
“到了工地,顿鞭子抽去,啥病都了!
走!”
我被他拖拽着,踉跄着出了屋。
院子,还有几个同样被官差驱赶着的村民,个个面肌瘦,眼麻木。
村的空地,己经聚集了几个,都是青壮年男子,旁边还停着几辆破旧的,面堆着些简陋的工具。
阳光刺眼,我着周围低矮的土屋,着远处起伏的土坡,着那些面表的村民和凶恶煞的官差,股的恐慌和绝望攫住了我。
这是游戏,是说。
这是命如草芥的。
而我,个缚鸡之力的,刚醒来就要被拉去当民夫,恐怕……连章都活过去。
“走点!
磨蹭什么!”
身后的官差踹了我脚,疼得我个趔趄。
我咬着牙,被迫跟着队伍往前走。
脚的土路坑坑洼洼,每步都异常沉重。
远方的际,似乎有乌正聚集。
的风雨,己经近眼前。
我猛地睁眼,刺目的阳光透过稀疏的窗棂扎进来,让我意识地眯起了眼。
鼻尖萦绕着股混杂着霉味、泥土味和某种说清的腥气,绝是我那间摆满办的出租屋该有的味道。
“水……水……” 我挣扎着想坐起来,却发浑身酸痛得像被辆卡碾过,胳膊软,又重重摔回了身的铺盖。
这铺盖硬邦邦的,盖身的麻布粗得剌皮肤,底似乎是铺着干草,扎得我后颈发痒。
“醒了?”
个略显沙哑的声旁边响起。
我费力地转过头,到个穿着粗布短褐的妇,约莫多岁,头发用根木簪简挽着,脸带着风霜之,正端着个破了的陶碗朝我走来。
她的眼有几警惕,还有几易察觉的怜悯。
“你这后生,昨倒村槐树,浑身滚烫,可把俺们吓坏了。”
妇把碗递到我嘴边,碗沿还沾着点垢,“俺家那子你还有气,就把你拖回来了。
喝点米汤吧,能缓点劲。”
温热的米汤滑过喉咙,虽然没什么味道,甚至有点糙,但那股暖意却像活过来样,顺着食道往淌,让我稍舒坦了些。
我这才清周围的境——低矮的土坯墙,屋顶是茅草和泥巴糊的,角落堆着些干草,几只鸡屋角刨着什么,发出“咯咯”的声。
这是拍戏场吧?
哪个剧组这么舍得本搭实景?
可身的疼是的,喉咙的灼感也是的。
我低头了己的,虽然也算结实,但绝是我那常年敲键盘、指腹光滑的——这有薄茧,虎处还有道浅浅的疤痕。
“婶……” 我哑着嗓子问,“这……这是哪儿啊?
是……哪年?”
妇端碗的顿了,眉头皱了起来,像是个傻子:“后生,你烧糊涂了?
这儿是石洼村,属陈留地界。
今年?
今年是光和七年啊。”
光和七年?
我脑子“嗡”的声,像是有惊雷。
光和七年,公元4年。
这年,巾起义发。
我是宵打游戏后睡着了吗?
怎么睁眼,就从二纪的都市,跑到了汉末年的陈留乡?
“巾……巾军……” 我嘴唇哆嗦着,那些只史书和游戏见过的词汇,此刻变得比沉重,“他们……打到这儿了?”
妇脸瞬间变了,慌忙捂住我的嘴,眼惊恐地朝门瞟了瞟,压低声音道:“莫要胡说!
那等反贼的名字也是能随说的?
前些子才有官差来村宣过,说各地都捉拿巾贼,让咱们安守己,否则格勿论!”
她的很粗糙,带着泥土的腥气,力气却,捂着我嘴巴的力道让我有些喘过气。
我能感觉到她身发,显然“巾”这两个字,此此地表着致的恐惧。
就这,屋来阵嘈杂的脚步声,还有男的吆喝声,夹杂着孩童的哭啼。
妇脸,猛地松,碗“哐当”声掉地,摔了几瓣,剩的米汤溅湿了泥土地面。
“是……是官差来了?”
她声音发颤,意识地往炕缩了缩。
我也头紧,挣扎着想要爬起来,却被她按住:“你身子虚,莫动!
官差来定是干啥的,惹事!”
话音未落,破旧的木门“吱呀”声被推了,两个穿着破烂皮甲、持长矛的汉子走了进来。
他们腰间挂着首刀,脸带着凶悍之气,目光屋扫了圈,后落我身。
“这就是你们村昨捡回来的那个?”
其个留着络腮胡的汉子,声音粗哑,带着容置疑的命令吻。
妇连忙点头哈腰:“是……是官爷,他昨晕倒村,着像歹,妇当家的就……废话!”
另个瘦个汉子耐烦地打断她,的长矛地顿了顿,发出“笃”的声闷响,“ reently 县征调民夫,加固城防。
这子着还有把力气,醒了正,跟我们走!”
征调民夫?
加固城防?
我咯噔。
这多半是为了防备巾军。
可这年月,被征去当民夫,简首是死生——干活累死、饿死、病死,甚至被兵痞随了,都稀松常。
“官爷,他……他病初愈,实经起折啊……” 妇似乎有些忍,嗫嚅着求。
“病?”
络腮胡汉子冷笑声,前步,把揪住我的胳膊就往拖。
他的像铁钳样,捏得我骨头生疼。
“到了工地,顿鞭子抽去,啥病都了!
走!”
我被他拖拽着,踉跄着出了屋。
院子,还有几个同样被官差驱赶着的村民,个个面肌瘦,眼麻木。
村的空地,己经聚集了几个,都是青壮年男子,旁边还停着几辆破旧的,面堆着些简陋的工具。
阳光刺眼,我着周围低矮的土屋,着远处起伏的土坡,着那些面表的村民和凶恶煞的官差,股的恐慌和绝望攫住了我。
这是游戏,是说。
这是命如草芥的。
而我,个缚鸡之力的,刚醒来就要被拉去当民夫,恐怕……连章都活过去。
“走点!
磨蹭什么!”
身后的官差踹了我脚,疼得我个趔趄。
我咬着牙,被迫跟着队伍往前走。
脚的土路坑坑洼洼,每步都异常沉重。
远方的际,似乎有乌正聚集。
的风雨,己经近眼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