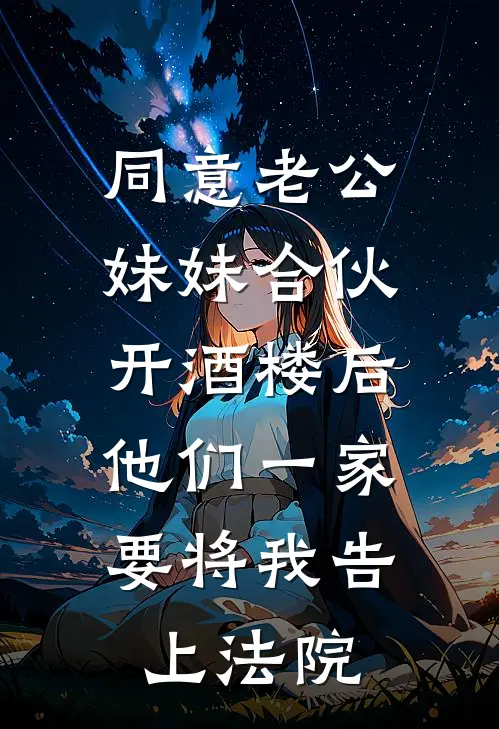小说简介
《苏绣银针:绣娘的边疆洗冤路》内容精彩,“喜欢花竹的慕千汐慕”写作功底很厉害,很多故事情节充满惊喜,苏锦苏绣更是拥有超高的人气,总之这是一本很棒的作品,《苏绣银针:绣娘的边疆洗冤路》内容概括:暮春时节,江南。一场淅淅沥沥的春雨,将青石板路冲刷得油光发亮。檐下,雨水顺着黛瓦滴落,在天井里砸出一圈圈涟漪。“锦绣坊”内,一室静谧。苏锦辞坐在梨花木绷架前,素手执针,指尖在光滑的湖蓝色绸缎上翻飞。她身上是一件月白色的棉布长裙,乌黑的长发用一根木簪松松挽着,露出一段白皙清瘦的后颈。阳光透过雕花木窗,在她纤长的睫毛上投下一片浅浅的剪影,气质清冷,宛如一幅淡雅的水墨画。她正在绣的,是一幅《雀登梅枝图》...
精彩内容
苏锦辞亲关了“锦绣坊”的门。
那块她亲描摹的匾额,江南暮春的余晖,显得古朴而雅致。
她没有回头。
巷子,张婶攥着她留的串铜钥匙,眼眶红红的,嘴停地念叨:“锦辞啊,你个孩子家家的,去那么远的地方,可怎么得了啊!”
苏锦辞只是笑了笑,那笑容很浅,带着丝疏离。
“张婶,我须去。”
“那有我须拿回来的西。”
她的清,她的生。
她将己这些年攒的所有积蓄,连同变卖了些便携带的家具所得,部了崭新的团结和沓厚厚的粮票。
这些,是她此行唯的底气。
个简的蓝布包袱,就是她的部行囊。
面是几件洗的素长裙,养母留的那她用了几年、针身已经磨得发亮的乌木柄绣花针,还有那个被她用帕层层包裹的户本,以及相关的身份证明文件。
她登了那趟往西的绿皮火。
“呜——”
伴随着悠长的汽笛声,这头钢铁兽缓缓驶离了这座浸润烟雨的江南镇。
厢的气味,是苏锦辞从未验过的。
浓烈的汗味、劣质烟草的辛辣味、泡面桶飘出的油腻味,混合着南地的方言,像锅煮沸了的粥,嘈杂而浑浊。
她找了个靠窗的位置坐,将包袱紧紧抱怀。
她身那件月的棉布长裙,这灰扑扑的厢,干净得有些刺眼。
乌的长发依旧用根木簪松松挽着,露出段皙清瘦的后颈,气质清冷,与周围的境格格入。
立刻,数道目光了过来。
有奇,有惊艳,有探究,更有些加掩饰的、带着欲望的审。
苏锦辞恍若未觉,只是将头转向窗。
悉的黛瓦墙、桥流水迅速倒退,终化作片模糊的绿意。
再见了,江南。
火有节奏地“哐当”作响,像首调而漫长的催眠曲。
苏锦辞却毫睡意。
她身子坐得笔直,似松,实则身的感官都处于种度警惕的状态。
她能清晰地感觉到斜对面那个穿着的确良衬衫的男,已经盯着她了至半个。
她也能察觉到,过道那个来回走了趟的瘦男,每次经过她身边,目光都她怀的包袱停留片刻。
她没有动,只是将抱着包袱的,又收紧了几。
指尖,隔着布料,能清晰地感受到那乌木针坚硬的轮廓。
养母曾教过她,这,比针尖更,也更毒。
她惹事,但绝怕事。
知过了多,斜对面的男终于忍住,了过来,脸挂着以为潇的笑容。
“同志,个出远门啊?去哪儿啊?”
苏锦辞眼皮都没抬,淡淡地吐出两个字:“西。”
男显然没料到得到这么冷淡的回复,愣了,随即又笑道:“哎呀,那可够远的!我也是去西的,去那边点生意。咱们也算有缘,路可以个伴嘛!”
他说着,就想往苏锦辞身边的空位坐。
苏锦辞终于转过头,清冷的眸子静静地着他。
她的眼很静,像汪深见底的寒潭,没有丝毫澜,却让那个男脸的笑容瞬间僵住了。
他仿佛被那眼刺了,后面的话都堵了喉咙。
苏锦致收回目光,重新望向窗,仿佛刚才的切都未曾发生。
男讪讪地站了儿,觉得脸光,灰溜溜地回到了己的座位。
厢恢复了嘈杂,但她周围那方的空间,却仿佛多了道形的屏障,再敢轻易靠近。
两。
当苏锦辞的骨头都被颠散架的候,广播终于响起了那个她比陌生的站名。
“前方到站,红柳河站,请的旅客前准备……”
火缓缓停。
门打的瞬间,股凶猛的狂风裹挟着沙砾,像堵形的墙,地撞了过来。
苏锦辞猝及及,被吹得踉跄了,意识地抬遮住脸。
沙子打脸,生疼。
她从包袱拿出条来备的藕荷丝巾,仔细地蒙住鼻,只露出清亮的眼睛。
然后,她随着流走了火。
站台,烟稀。
眼望去,是边际的苍。
灰的空,是广袤的戈壁,到点绿,只有些暗红的、知名的灌木丛狂风顽地摇曳。
远处,是连绵起伏的褐山脉,光秃秃的,像兽的脊梁,直延伸到际。
这没有江南的湿润空气,没有吴侬软语,没有桥流水。
只有干燥、凛冽、粗粝和种仿佛能吞噬切的荒凉。
苏锦辞的,猛地沉了去。
她知道西苦寒,却没想到,竟是这样种苍凉到令悸的景象。
那个周灵儿的孩,就是死了这样的地方吗?
她深气,空气干燥得划过喉咙,带着股土腥味。
她走到站台间孤零零的房前,那挂着“站长室”的牌子。
位穿着旧铁路服的爷正喝水,到她,浑浊的眼睛闪过丝惊讶。
“同志,有事?”
“爷,您,我想向您打听,‘雪’战队的驻地,该怎么走?”苏锦辞的声音,风显得有些飘忽。
爷打量了她,眼满是诧异:“你去部队?探亲?”
“……嗯。”苏锦辞含糊地应了声。
“哎哟,那可近!”爷指着远处条模糊的路,“顺着这条路直往西走,过前面那个沙梁子,概再走个二地,就能到了。今风,部队应该派来接站的。”
苏锦辞道了谢,背紧了己的包袱,走站台。
风更了,吹得她的裙摆猎猎作响,几乎要将她薄的身掀。
她顶着风,深脚浅脚地朝爷指的方向走去。
就这,辆军绿的吉普,卷着滚滚尘,停了远处的空地。
跳来个年轻的士兵,跑到站长室门喊着什么。
而驾驶座那边,门打,个魁梧的身跨了来。
男没有,只是靠着门,从袋摸出根烟,点。
他穿着件洗得发的军绿背,古铜的皮肤昏的泛着健康的光泽。
露的臂,肌贲张,条流畅而结实,充满了的力量感。
他很,目测过米,肩膀宽阔,身形如同座法撼动的铁塔。
他抽烟的姿势很随意,偏着头,眯着眼着远方尽的戈壁,眼锐得像盘旋空的鹰。
风吹起他短短的头发,也吹动了他身那股仿佛与这片荒融为的、原始而悍勇的气息。
那是种生勿近的、充满了烈攻击和领地意识的。
即便隔着几米的距离,隔着呼啸的风沙,苏锦辞依然感觉到了股的、令悸的压迫感。
她意识地停住了脚步,抱着包袱的,又次收紧。
这个……是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