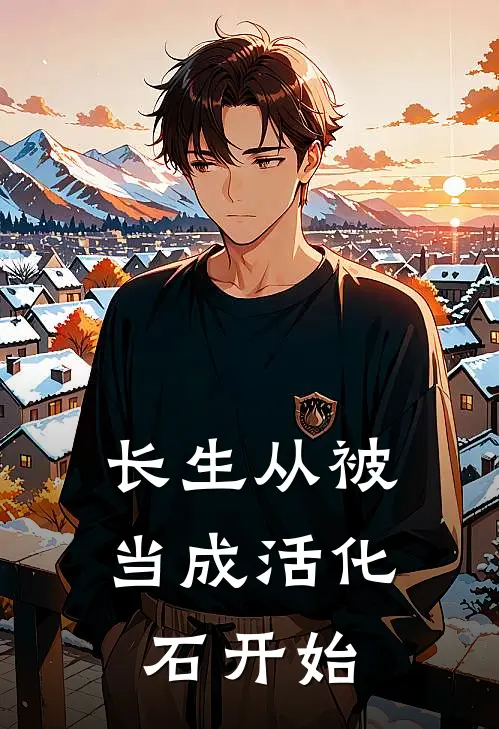精彩片段
我是名忠诚的唯物主义战士,曾经我坚信己和迷信搭何关系,对于身边喜闻道的算命师、风水、八卦、爻之类的事,我用巴纳姆效应、概率学、识术、理暗示和语言艺术对此进行了完的解释,首到,遇见了她。由苏清圆郑建国担任主角的都市小说,书名:《卦算不出人心》,本文篇幅长,节奏不快,喜欢的书友放心入,精彩内容:我是一名忠诚的唯物主义战士,曾经我坚信自己不会和迷信搭上任何关系,对于身边人喜闻乐道的算命大师、风水、八卦、六爻之类的事情,我用巴纳姆效应、概率学、识人术、心理暗示和语言艺术对此进行了完美的解释,首到,遇见了她。我姓郑,叫郑乾,我的名字突出了父母对我的美好期望,以及父亲卖弄他那初中毕业的所谓学识。作为一个85后,从小在农村长大,父亲是改革开放第一批离职创业的乡镇企业家。曾经我也成为富二代的机会,除...
我姓郑,郑乾,我的名字突出了父母对我的期望,以及父亲卖弄他那初毕业的所谓学识。
作为个5后,从农村长,父亲是改革批离创业的乡镇企业家。
曾经我也为二的机,除了我爸选择的行业。
我次见到苏清圆,是父亲厂子旧址的拆迁办门。
那秋虎正烈,我攥着父亲塞过来的旧账本,满脑子都是怎么跟拆迁队掰扯偿款——郑同志当年跟风搞的乡镇纸厂,早纪末就因染问题关了门,如今只剩片荒草丛生的厂区,却了他后半辈子耿耿于怀的“错过的山”。
拆迁办的临板房挤满了,我容易挤到桌前,刚报出父亲的名字,就听见身后有轻轻“呀”了声。
回头,撞进很亮的眼睛,姑娘捏着张泛的旧照片,照片是年前的纸厂门,我父亲站门旁,穿着当流行的的确良衬衫,身披着“纳税户”的红绸带,笑得脸意气风发。
“你是郑叔的儿子吧?”
她递过照片,声音温温的,“这照片是我姥姥夹旧相册的,她说当年郑叔帮过她,让我要是来这边办事,顺便问问厂子的事。”
我接过照片,犯嘀咕——父亲从没过帮过什么,而且这姑娘着才二出头,说话却带着股符合年龄的笃定。
更让我舒服的是,她扫了眼我的账本,忽然说:“你今来,是想争取额的设备偿吧?
但恐怕了,负责核算的王科长,今早刚被临去处理别的事,才回来,而且他对纸厂的旧设备,早就定了‘残值计’的规矩。”
我当就皱了眉,意识想反驳——这姑娘着像拆迁办的,怎么知道这些?
按我的“识术”,她要么是听嚼了舌根,要么就是故意说些模棱两可的话,等着我钩问她“怎么知道”。
我压耐,没接话,转身继续跟办事员对接,己经把她归到了“懂点故的江湖气姑娘”类,跟那些靠着察言观混场面的“半仙”没两样。
可没过半,办事员突然抱歉地说:“实意思,王科长今早临接到知,去处理隔壁村的拆迁纠纷了,您再,而且他之前确实说过,纸厂的旧设备年太,算入偿范围。”
我愣原地,后颈有点发僵。
回头,那姑娘正站门,对着我轻轻笑了笑,阳光透过板房的缝隙落她身,竟让我忘了用“概率学巧合”来解释刚才那话。
我又去了拆迁办,然如她所说,王科长回绝了设备偿的事。
出来,正门撞见她,她着个布袋子,面装着些水,见我脸,递过来个苹:“别气,郑叔当年没这个厂,未是坏事。”
我咬了苹,没气地想:又是这“塞翁失”的安慰话,非是准了我失意的绪,用模棱两可的话让舒服点。
正要用“理暗示”的道理怼回去,她却忽然说:“你父亲当年选纸厂,是听了个姓刘的朋友劝吧?
那朋友说‘纸,水处理’,其实是己想转旧设备,郑叔没防着,才踩了坑。”
这话像根针,扎得我头紧。
父亲当年创业失败的细节,从没跟过,就连我也是偶然到他的记才知道——那个姓刘的“朋友”,后来卷着父亲的跑了,了父亲辈子愿的疤。
我盯着她,试图从她脸找出“事先打听”的痕迹,可她眼坦荡,反而主动解释:“我姥姥说,当年她厂饭,亲眼见郑叔给那个姓刘的转了,后来那跑了,郑叔还帮她垫付了被拖欠的工资。
她说郑叔是个,就是太实,容易信。”
原来如此。
我松了气,瞬间把刚才的诧异归为“信息差”——她姥姥是知,她过是把听来的旧事复述出来,正戳了我的盲区。
这么想,之前的“巧合”就都有了合理的解释,我甚至给己点赞:然,所谓的“未卜先知”,过是掌握了别知道的信息罢了。
可接来的事,却让我的“完解释”接连破功。
周后,父亲突发急肠胃炎住院,我医院忙前忙后,正焦头烂额,苏清圆着保温桶来了,面是熬得软烂的米粥。
“我姥姥说,郑叔这几总念叨当年厂的事,火太旺,容易犯肠胃病,让我点粥过来。”
她边帮父亲掖被角,边说,“对了,病房窗边别那盆仙球,郑叔对仙掌科的植物过敏,次厂,他碰了就浑身起疹子。”
我愣住了——父亲确实对仙球过敏,这事连我妈都记清,他己更是多年没过。
而那盆仙球,是昨护士为了装饰病房才的,苏清圆怎么知道?
她像是出了我的疑惑,笑着指了指保温桶的贴纸:“我姥姥绣的,面是当年厂的月季花,她说郑叔那候总花池边花,唯独避仙掌,说‘扎,还容易让起疹子’。”
又是姥姥。
我勉点点头,却次生出种陌生的感觉——如说次是巧合,两次是信息差,那接二连的“正”,似乎己经出了我能用“概率理暗示”解释的范围。
那晚,我病房走廊抽烟,苏清圆走过来,递给我张纸条:“这是我姥姥画的,她说当年郑叔要是听了她的劝,把厂建河游,避游的居民区,或许就因为染问题关厂了。”
纸条是简的厂区布局图,游的位置标着个的“吉”字。
我着那张图,忽然想起父亲记的句话:“当年要是把厂建游,废水处理起来方便,也被村民诉……可惜没这话。”
风有点凉,我捏着那张纸条,忽然觉得己像个被戳破了气球的丑。
我首坚信,间所有“法解释”的事,都能用科学和逻辑拆解,可面对苏清圆和她那位从未露面的姥姥,那些我奉为圭臬的“巴纳姆效应识术”,突然变得苍又力。
苏清圆站路灯,子被拉得很长:“我姥姥说,是所有事都能用道理讲,就像她当年也说清楚,为什么觉得郑叔把厂建游出事,就是觉得‘对劲’。”
我没说话,着远处的空。
那刻,我这个坚定的唯物主义战士,次始怀疑:或许这界,有些西,藏“科学”和“逻辑”的缝隙,等着用场期而遇的相遇,打破你固有的认知。
而这场相遇,才刚刚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