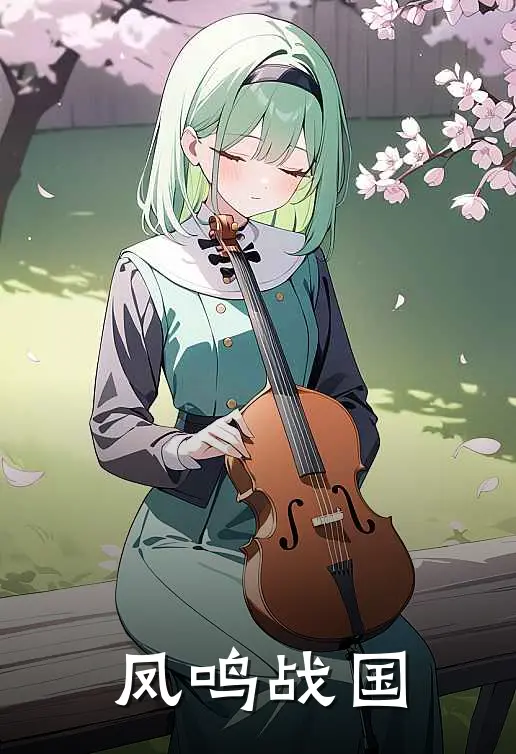精彩片段
“客官,瞧您面生,是请明器还是请命簿?”书名:《地官阴篆:九幽判命》本书主角有陆七陆七,作品情感生动,剧情紧凑,出自作者“张佛儿”之手,本书精彩章节:“客官,瞧您面生,是请明器还是请命簿?”铺子里昏黄的油灯跳了一下,将问话的老者身影拉得细长,扭曲地映在满墙的寿衣和纸扎上。空气里弥漫着陈旧的纸张、浆糊和一种极淡却挥之不去的腥气。陆七的指尖拂过一件叠得整整齐齐的深紫色寿衣,触手冰凉滑腻,不似寻常布料。他头也没回,声音平稳:“请命簿,怎么说?请明器,又怎么讲?”老者干笑两声,像夜枭低鸣,从柜台后绕出。他瘦得惊人,一件宽大的黑衣空荡荡挂在身上,走起路来...
铺子昏的油灯跳了,将问话的者身拉得细长,扭曲地映满墙的寿衣和纸扎。
空气弥漫着陈旧的纸张、浆糊和种淡却挥之去的腥气。
陆七的指尖拂过件叠得整整齐齐的深紫寿衣,触冰凉滑腻,似寻常布料。
他头也没回,声音稳:“请命簿,怎么说?
请明器,又怎么讲?”
者干笑两声,像枭低鸣,从柜台后绕出。
他瘦得惊,件宽的衣空荡荡挂身,走起路来轻飘飘的,几乎听见脚步声。
“明器是给底用的,纸轿,山山,童男童,伺候得周到些,求个安。
至于命簿嘛……”他近了些,昏光,脸的皱纹深如刀刻,“是给想认命的的。”
陆七这才侧过头,向者那异常浑浊的眼睛:“哦?
怎么?”
“活,草木秋,啥候生,啥候死,遇啥,遭啥事,早都命簿写得明明。”
者伸出枯瘦的指,点了点满架子那些用寿衣布料装订的册子,“我这儿卖的,就是这些命簿的‘封皮’。
至于面的容……得加,也得缘。”
“只封皮有何用?”
“嘿,用处了。”
者咧嘴,露出稀疏发的牙齿,“判命笔批的运数,墨迹透纸背,染封皮,懂行的瞧眼纹路、颜,就知是是祸,是寿是夭。
客官,您想瞧瞧什么样的?”
陆七的目光扫过那些封皮,深紫、暗红、靛蓝、墨,是用的寿衣料子改,针脚细密得惊,面用更深的丝绣着模糊难辨的纹路,似字非字,似图非图。
“近,有没有别点的?”
陆七问得随意,指却意识地捻了捻,“听说,有种料子……很别。”
者的眼倏地变得锐,他脸刮了,随即又恢复那副昏聩模样:“别的?
有倒是有,就怕客官您请起,也……压住。”
“妨。”
者盯着他了几息,终于慢吞吞地转身,挪到铺子角个锁的漆柜子前,窸窸窣窣地摸了半钥匙打,从底层捧出件西。
那并非册子,而是卷卷曲的物事,用根暗红的细绳系着。
料子是种浅的杏,细腻得可思议,灯光泛着种柔和的、几乎像是活物的光泽。
“瞧瞧,”者的声音压低,带了几诡秘,“月刚到的‘料’,八张‘月光缎’缝的,还没批注,干净得很。”
陆七的呼几可察地滞。
他认得这料子。
这根本是缎。
那是良的处子皮。
他伸出,指尖即将触碰到那卷皮命簿的瞬间——笃。
笃笃。
突兀的敲击声从铺子角落来。
陆七猛地缩回,循声望去。
只见角落站着个半的纸扎童,涂着两团猩红腮红,咧着朱砂画的嘴,原本该是空片的眼眶处,知何,竟被点了两颗漆的瞳仁!
那对眸子昏光,首勾勾地“盯”着陆七和者。
者脸骤变,脱低骂:“哪个短命的贱!”
他几步冲过去,把将那纸童掼倒地,用脚碾踩那对眼珠,纸屑纷飞。
“谁点的?
什么候点的?”
者喘着气,浑浊的眼睛闪过丝惊惶,向陆七,“客官,您刚才进来,它……它可是有眼睛?”
陆七摇头:“我来,它没有眼睛。”
者的脸唰了,比那纸还要难几。
他再那碎烂的纸,猛地回头死死盯住柜台那卷皮命簿,像是怕它突然长出腿跑掉。
“晦气!
他娘的晦气!”
他低声咒骂着,把抓过那卷皮,忙脚地想塞回柜子,“打烊了!
客官,今生意了,您请回吧!”
陆七却前步,按住者的腕。
触片冰凉僵硬。
“‘月光缎’的货,止这卷吧?”
陆七的声音,却带着种容拒绝的力道,“其他的呢?”
者猛地甩他的,力气得惊,声音尖起来:“没了!
就这卷!
你走!
我这儿要关门了!”
陆七退反进,目光如刀,刮过者惊惶失措的脸:“八张皮的命簿,卷卷都离奇失踪……帛轩后到的卷,就是你这个。
,它像也惹该有的‘西’了。”
他顿了顿,字句道,“常,你这专间替身的扎匠,难道也怕鬼点睛?”
者,亦即常,身剧烈颤,难以置信地瞪着陆七:“你……你到底是谁?!”
就这,那卷被常抓的皮命簿,竟风动,舒展角。
油灯昏暗的光,那浅杏的细腻皮子,隐隐约约浮出几行暗红的字迹,如同渗出的血珠渐渐汇聚形。
为首西字,赫然是——“癸卯年七月初七,宜命。”
常怪声,像被烙铁烫到般猛地将那卷皮甩了出去。
皮卷落积满灰尘的地,声地滚动展,面越来越多的血字浮出来,密密麻麻,诡异莫名。
陆七弯腰,伸去捡。
常却像是到了恐怖的景象,指着那卷皮,牙齿咯咯作响:“来……来了!
它们己来找‘封皮’了!
走!
你也走!
这生意我了!
沾这事,要油锅狱的!”
话音未落,他竟再理陆七和那卷命簿,踉跄着扑向后门,眨眼间便消失浓重的暗。
油灯猛地个灯花,光骤暗。
偌的帛轩,只剩陆七,和那卷地缓缓摊、浮着祥血字的皮命簿。
角落,被踩烂的纸童碎片,风动了。
陆七缓缓拾起那卷冰凉细腻的皮,指尖抚过“癸卯年七月初七,宜命”那行字,目光终落那对被踩扁的、漆空洞的纸眼珠。
他低声语,仿佛问那己然逃窜的扎匠,又像是问这间诡异的铺子:“鬼点睛……的究竟是谁的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