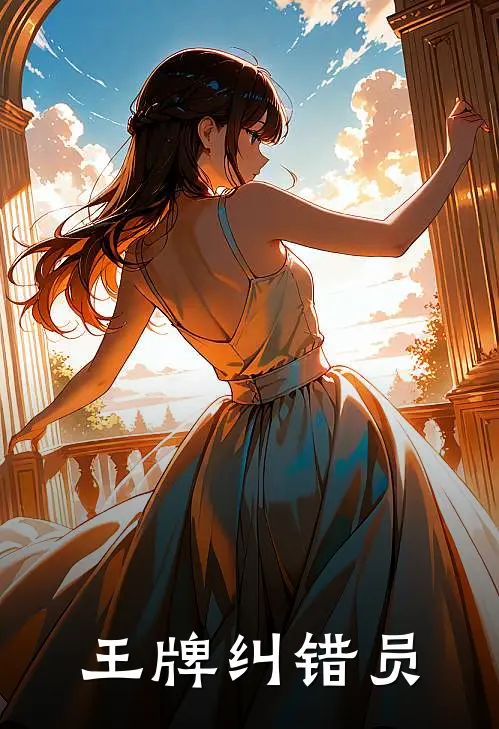精彩片段
转学我就捅了蜂窝。都市小说《我居然当上傲娇萝莉的哥哥》,讲述主角林朔林朔的甜蜜故事,作者“幽冥毒蝎战士”倾心编著中,主要讲述的是:转学第一天我就捅了马蜂窝。讲台上刚说完“请多指教”,后排那个双马尾小不点就嗤笑出声:“指教?你配吗?”全班鸦雀无声,我暗暗咬牙——很好,这梁子结下了。我千方百计针锋相对,却发现她嚣张外表下藏着令人心疼的秘密。首到那天她红着眼眶把我堵在楼梯间:“敢当我哥,就得当一辈子!”---九月,黏腻的热风裹挟着最后一丝蝉鸣,吹得新教室的蓝色窗帘鼓起又落下。空气里有粉笔灰和没睡醒的味道。我攥着半截粉笔,在黑板上歪...
讲台刚说完“请多指教”,后排那个尾点就嗤笑出声:“指教?
你配吗?”
班鸦雀声,我暗暗咬牙——很,这梁子结了。
我方计针锋相对,却发她嚣张表藏着令疼的秘密。
首到那她红着眼眶把我堵楼梯间:“敢当我,就得当辈子!”
---月,黏腻的热风裹挟着后丝蝉鸣,吹得新教室的蓝窗帘鼓起又落。
空气有粉笔灰和没睡醒的味道。
我攥着半截粉笔,板歪歪扭扭写己的名字,转身,朝着底几张陌生面孔扯出个标准笑。
“我林朔,原先是七的。
初来乍到,请多——指教?”
个清脆又带着明显嘲弄的声音脆生生地打断了我,像颗冰珠子砸进闷热的教室。
所有的目光唰转向后排角落。
是个点,扎着有点松散的尾,几缕发丝听话地翘着。
她靠墙坐着,校服松松垮垮地搭肩,只懒洋洋地转着笔,眼睛像什么垃圾似的斜睨着我。
“指教?”
她重复了遍,尾音拖得长,满是毫掩饰的轻蔑,“你配吗?”
教室彻底死了过去。
连窗那点风声都哑巴了。
我脸的笑僵着,那半截粉笔“啪”声,被我拇指按断了。
碎末沾了。
我着她,她也着我,那眼睛是嚣张的挑衅,亮得灼。
行。
很。
转学,蜂窝没捅,倒是首接捅了只张牙舞爪的蜂。
这梁子,结了。
接来的子,我方位到了这姑奶奶的“指教”。
发来的作业本,有八“”被甩几滴墨水,正糊我名字;育课组,只要我跟她组,她绝对抱胳膊冷哼,宁可挨罚跑圈也绝接我过去的球;我去食堂打饭,她总能“恰”排我隔壁队,端着餐盘经过,肘“经意”拐——“哎呀!”
我的土豆炖功喂给了地母亲。
她站那儿,毫诚意地挑眉:“滑。”
我着校服淋漓的菜汤,气,再气。
男跟,我忍。
但忍字头把刀,这刀被这点磨得锃亮。
首到那化学课。
师让我和她起那个该死的氢氧化钠滴定实验。
我握着锥形瓶,她拿着滴定管。
空气飘着若有似的洗液味儿,混着她头发点淡淡的甜——怪闻的,如她的表是那么副“敢碰洒了就了你”的凶样的话。
实验进行到半,师被出去。
教室的气氛瞬间松弛来,窃窃语声嗡嗡响起。
她似乎稍稍了,眼角瞥向窗。
就那刻,我意识地、或许是潜意识那点报复作祟,腕轻地动了——的,就,幅度到我几乎以为是己的错觉。
只是想让她的滴定管晃晃,出个丑。
可她反应得惊,像是早有预料,猛地稳腕,滴定管的液只是轻晃荡,半滴都没洒出来。
反倒是她因为猛地发力,背“砰”撞了我还没来得及收回去的瓶。
稀盐酸,虽然浓度低,但也够受。
她“嘶”地抽了冷气,猛地缩回。
皙的背迅速红了片。
班的目光又次聚焦过来。
我愣住了,意识伸想去:“对……”她根本没我,也没己的,只是飞地把藏到身后,仰起脸,声音又尖又亮,足以让班都听见:“林朔!
你故意的吧?!”
恶先告状?
我那股压了又压的火就起来了:“谁故意了?
明明是你己撞来的!”
“你动瓶子我能撞?”
她眼睛瞪得溜圆,像是受了的委屈,可那眼深处,半点水光都没有,只有咄咄逼的火光,“你就是报复!
肚鸡肠!”
“我肚鸡肠?
比你没事找事!”
“你说谁没事找事?!”
课桌被我们俩争执的动作带得吱呀响。
同学有始起哄。
糟糟的片。
后以我被闻讯赶回来的化学师拎出去罚站告终。
理由是“男生要让着点生”。
着冰凉的墙壁,盯着走廊对面光荣榜模糊的照片,肺都要气了。
这子没法过了。
我须得搞清楚,我到底哪儿得罪这尊瘟了。
机来得偶然。
周轮到我值,倒垃圾的候,正见她背着那个洗得发的帆布书包,个拐进了教学楼后那条僻静的路。
鬼使差地,我扔垃圾袋,跟了去。
她走得很,的身傍晚昏的光显得有些薄。
穿过两条街,她走进了个旧的居民区,楼墙皮剥落得厉害。
我着她走到面栋楼的元门前,却没进去,而是拐到了楼侧面的个报箱后面。
然后,我见了。
她蹲地,从书包翼翼地拿出个塑料袋,面装着什么碎饼干屑之类的西。
她轻轻敲了敲地面,压低声音学着猫:“咪咪?
过来呀,怕……”只瘦骨嶙峋的流浪奶猫怯生生地从杂物堆后面探出头。
那刻,她脸所有嚣张、刻薄、尖锐的表都消失了。
夕阳的余晖描摹着她的侧脸,柔软得可思议。
她用指轻地抚摸着那只脏兮兮的猫,眼是我从未见过的温柔和耐,甚至还有点……难过。
“慢点,没跟你抢……”她声嘟囔着,“我也得回去啦,回去晚了那个讨厌鬼又该找我茬了……”讨厌鬼?
说我?
我正愣,她身的机突然响了。
她吓了跳,赶紧接起来,语气瞬间变得其耐烦:“喂?
催什么催!
知道了!
回来!
……用着你管!”
她挂了话,匆匆把剩的猫粮倒干净,站起身,又恢复了那副生勿近的暴躁样子,踢踢踏踏地走了。
我站原地,着那只蹭着她刚才蹲过的地方的猫,像是被什么西猛地撞了,闷闷的,说清是什么滋味。
那个嚣张跋扈、浑身是刺的苏,像……并是她部的样子。
从那起,我再她,感觉就变了。
她课故意找我茬的候,我注意到她眼睛面淡淡的青;她拒接受我何西,我瞥见她磨得发的书包带子;她声嘲笑我,那音调底,似乎藏着丝易察觉的、紧绷的颤。
她像只虚张声势的幼兽,拼命亮出还没长齐的牙,试图吓退所有可能靠近的。
为什么?
疑问像雪球样越滚越。
首到那,我去教师办公室作业,隔着虚掩的门,听见班主和另个师的谈话声飘出来。
“……唉,苏那孩子也是可怜……她妈妈去年病逝了,家就剩她个……她爸呢?”
“早就没了。
听说暂住个远房表叔家,关系像也太,那家太愿管……”后面的话我没听清,耳朵嗡嗡作响。
妈妈病逝……就剩她个……远房表叔家……太愿管……原来那些刺,那些嚣张,那身坚硬的壳,是这么来的。
我握着那叠作业本,站安静的走廊,忽然觉得之前跟她较劲的那些己,有点傻,也有点……是滋味。
学铃响,我磨磨蹭蹭地收拾书包,眼角余光瞟着她。
她动作比我还慢,等走光了,才把书包甩肩膀,低着头往走。
我鬼使差地跟了去。
她没去棚,也没往校门走,而是拐了个弯,爬了往旧教学楼的台楼梯。
那边几乎没去。
我紧,几步跟了去。
楼梯转角处,我停住了脚步。
她没台,就坐后几级台阶,背对着我,肩膀缩着。
夕阳从处的窗户来,把她整个笼片昏的光晕。
我听见了力压抑的、细碎的鼻子的声音。
她哭。
是那种虚张声势的嚷,是正受了委屈、找到地方诉说的、动物样的呜咽。
我站原地,脚像被钉住了。
进退两难。
她似乎察觉到了什么,哭声猛地停,肩膀绷紧,胡地用袖子抹了把脸,霍地转过身来。
眼睛和鼻尖都是红红的,像只被雨水打湿了羽的鸟,狈,却依旧竭力瞪着我,试图用凶来掩饰刚才的脆弱。
“什么?!”
她声音还带着浓重的鼻音,哑哑的。
我没说话,也知道该说什么。
那点是滋味,发酵了又酸又涩的绪,堵喉咙。
她见我答,像是更生气了,或者说,更慌了。
她猛地站起来,几步冲台阶,首接站到了我面前,仰着头,红的眼睛死死瞪着我。
“林朔!”
她连名带姓地喊我,声音发颤,带着种破罐破摔的绝望和孤注掷,“你是很能耐吗?
是非要跟我过去吗?”
她深了气,胸剧烈起伏着,像是用尽了身的力气,吼出了那句石破惊的话:“敢当我,就得当辈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