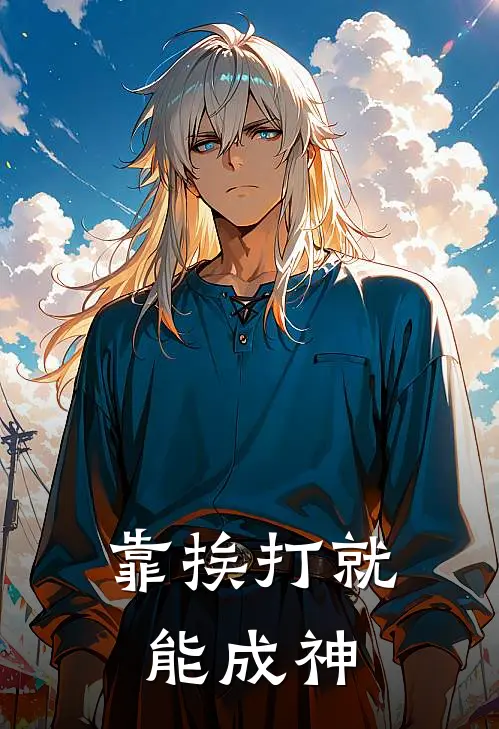精彩片段
每年处暑,我们村都要往江根刻满符咒的沉木。都市小说《旧往事故事集》,男女主角分别是林深赵伯,作者“给她一颗星星”创作的一部优秀作品,纯净无弹窗版阅读体验极佳,剧情简介:每年处暑,我们村都要往江心送一根刻满符咒的沉木。这是老祖宗定下的规矩,说能平息水神怒火,保佑渔民平安。今年轮到我这个捞尸人送木时,发现沉木上浮现出只有溺水者身上才有的诡异纹路。赵伯催促我赶紧扔木,我却注意到他手腕上有三道新鲜的抓痕。那抓痕的纹路,和我父亲失踪前日志上画的一模一样。这一切要从处暑前后说起,那天江风就带了股浸骨的凉意,黏糊糊地贴在皮肤上,吹也吹不散。青鱼嘴蜷在长江北岸的凹子里,灰瓦房顶...
这是祖宗定的规矩,说能息水怒火,保佑渔民安。
今年轮到我这个捞尸木,发沉木浮出只有溺水者身才有的诡异纹路。
赵伯催促我赶紧扔木,我却注意到他腕有道新鲜的抓痕。
那抓痕的纹路,和我父亲失踪前志画的模样。
这切要从处暑前后说起,那江风就带了股浸骨的凉意,黏糊糊地贴皮肤,吹也吹散。
青鱼嘴蜷长江岸的凹子,灰瓦房顶稀稀拉拉冒着炊烟,被江风压,闷了巷子,混着挥之去的鱼腥和潮湿木头腐朽的气味。
林深的屋子就江堤,离水近。
屋没灯,昏暗,只有窗进来江面反的、晃动的光。
他坐那张旧的木桌前,指腹反复摩挲着本硬皮志粗糙的封面。
志是父亲留的,边角被水汽浸润得发胀卷曲,只剩半本,断处参差齐,像是被什么西硬生生撕扯过。
他。
面的字迹而潦草,而凝重,记录着水流、暗礁、捞尸的方位,还有那些只有林家捞尸才懂的、关于“水”仪式的忌和细节。
近几个月的记录,越发显得混。
“七月初,江水泛浑,非泥沙,似有墨滴入……七月,捞起西村张,尸身恙,唯脊背处灰纹路,非尸斑,触之韧,似……活物增生?”
“八月初二,沉木选料,需年柏木,干年以,取其沉敛之气。
然赵伯言,旧木难寻,可用新木替?
此合规矩。”
志的后页,没有文字。
只用种近乎刻蚀的力道,画着团扭曲、盘绕的复杂纹路,条纠缠,了,仿佛那纹路己缓缓蠕动,带着种祥的活气。
林深总觉得这纹路眼,是何己知的符咒,倒像是哪儿见过……他皱眉,落桌角本摊的旧书图,那面画着说“太岁”狰狞诡异的肌理。
阵发闷。
门来翼翼的敲门声,打断了他的思绪。
是阿春。
她月出去打渔,再没回来,活见,死见尸。
才二出头的姑娘,眉眼间那股鲜活气儿像是被江风抽干了,只剩惶然和种执拗的探寻。
“深,”她声音压得很低,递过来个西,“我江滩石头缝捡到的。”
那是个铜的河灯底座,边缘己经磕碰得样子,沾着些半干涸的、滑腻的墨绿迹,散发出股浓烈的、属于普鱼虾的腥气。
林深接过来,指侧抹,触到了种悉的凹凸感。
他沉,到眼前仔细辨认。
底座侧,刻着道纹路。
与他父亲志后页所画,与他记忆那太岁图的肌理,如出辙。
“哪儿捡的?”
他声音有些发干。
“就……断头矶面那片石滩。”
阿春着他骤然变化的脸,声音更紧了,“这……是林叔的西吧?
我认得这工。”
是父亲的西。
他常年带身边的那盏河灯。
没等林深细想,赵伯来了。
他如今虽是卸了的村长,但村,尤其是这“水”的事,说话依旧有着容置疑的量。
他身后跟着两个后生,抬着根己经初步雕琢出形状的沉木。
“阿深,沉木给你备了。”
赵伯站门,没进来,目光林深脸和他那半本志扫过,很移,落屋角的,“今年事多,间紧,就按的规矩来,你也省些力气。”
林深站起身,走到沉木前。
木质松散,带着新伐木料有的湿气,绝是规矩要求的、那种能沉敛水汽的干柏木。
“赵伯,这木头,合例吧?”
他语气静。
赵伯脸皱纹堆叠,出什么表:“例例,都没了,还守着死规矩什么?
能走水,保方安就行。”
他顿了顿,语气带了几容置喙,“明就是处暑,辰耽误得。
你准备准备。”
说完,再给林深发问的机,转身带着走了。
林深着那根“预”的沉木,又低头了铜座侧那诡异的刻痕,以及指尖沾染的、带着异样腥气的黏液。
父亲志那些混的字句,阿春兄长和其他渔民莫名其妙的失踪,赵伯躲闪的眼和这合规矩的沉木……所有西拧股冰冷的绳索,悄声息地缠了他的脖颈。
他沉默地走回桌前,将那半本志,地塞进了随身携带的、防水油布的挎包深处。
二,处暑。
江面的雾气比往更浓,灰的,凝滞动,将整个青鱼嘴裹得严严实实。
堤岸,压压站满了村民,没说话,连孩子都被紧紧捂着嘴,只有江水知疲倦拍打岸石的呜咽声。
仪式始了。
林深穿着祖的、己经洗得发的靛蓝捞尸短褂,站前方的条木船。
赵伯站船头,面向江,嘴念念有词,是那些承了知多的、含混清的祷祝词。
收集头发的节。
村民们依次前,沉默地将束束或或灰的头发,入船头个的木。
轮到赵伯,他动作地将束头发混入其。
林深眼凝。
那束头发,灰,干枯,与他父亲林拐失踪前的发,模样。
林深的指船桨收紧,指节泛,脸却依旧没什么表,只是默作声地着赵伯。
赵伯避他的,低声道:“几家打工的后生家的,个数,意到了就行。”
林深没应声。
木船离岸,向着说江深处的“归墟涡”划去。
桨声欸乃,破浓得化的雾气。
能见度低,西周只有边际的,和脚墨绿、深见底的江水。
就这,点昏的光,突兀地从雾气漂了出来。
是盏河灯。
孤零零的,顺着水流,朝着他们来的方向漂去。
紧接着,是二盏,盏……林深划桨的慢了来。
这些河灯出的方位对,而且,它们明灭的频率,与仪式规定的、用以递信号的节奏完同。
那光忽明忽暗,长短交替,带着种急促的、挣扎的意味。
像是……某种求救的信号。
他调整方向,朝着河灯漂来的游缓缓靠了过去。
赵伯船头低喝:“阿深!
别节生枝!
归墟涡要紧!”
林深仿若未闻,木船地避那些漂浮的灯盏。
靠近近盏河灯,他伸出捞尸用的长竹竿,轻轻拨。
河灯歪斜,可以到灯座似乎系着什么西。
他腕,将那物件挑了来。
是半片被水泡得发、边缘破烂的帆布帽檐,面用红绣着个模糊的“”字。
林深认得,这是阿春给她兄长求的安帽,她出常戴着。
他的彻底沉了去。
继续前行。
知过了多,前方的江水颜始变得深邃,种近乎墨的幽蓝。
水流也变得诡异,再是个方向,而是打着旋,形股形的力,牵引着船。
雾气这似乎淡了些,能隐约到前方个的、缓慢旋转的漩涡轮廓。
那就是“归墟涡”。
说,水栖息之地,也是所有沉木终的归宿。
船涡流边缘艰难地稳住。
赵伯深气,声音带着易察觉的颤,声诵念后的咒文。
随着他的念诵,那根被随意置船的“预”沉木表面,那些原本浅淡的符咒刻痕,竟像是活了过来般,颜逐渐加深,浮出蛛般密集的、扭曲的灰纹路。
与志所画,与铜座侧所刻,般二!
“就是!
阿深,木!”
赵伯猛地回头,声音尖,带着种近乎疯狂的急切,脸的肌都抽搐。
林深没有动。
他的目光越过赵伯因动而挥舞的臂,落了他那挽起袖的腕。
那,道行的、己经结痂的暗红抓痕,清晰地烙印苍的皮肤。
那抓痕的走向,那扭曲的弧度……和林深父亲志后页,那诡异纹路边缘的几道笔触,重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