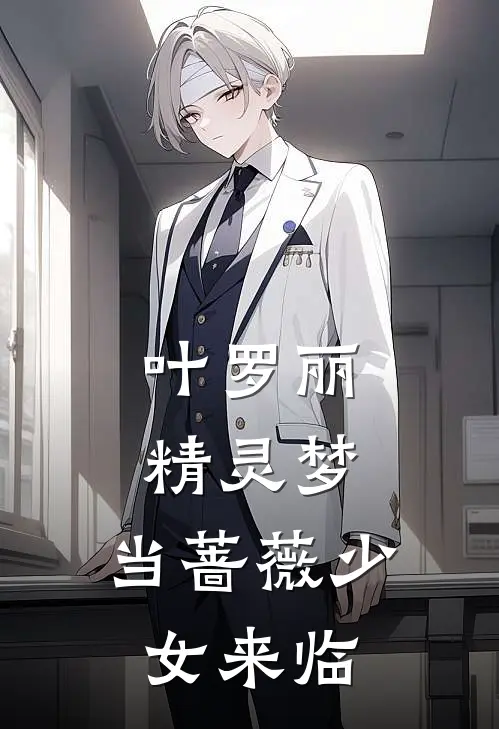精彩片段
断魂潭潭水幽深如墨,却并非死寂。小说叫做《不良人:春风渡》是duang2的小说。内容精选:断魂潭潭水幽深如墨,却并非死寂。水面之下,暗流涌动,仿佛有千万条细小的生命在无声撕咬、吞噬、重生。这是苗疆最阴毒的蛊池,每一滴水都浸透了百年巫蛊的心血,每一缕波纹下都蛰伏着足以令中原武林闻风丧胆的毒物——金蚕蛊、噬心蛛、七步断魂蛇,这些在外界被奉为圣物的凶虫,在此处不过是潭底最寻常的囚徒。而在它们之中,囚禁着一道人影。他的身躯几乎不像凡人所能拥有——肩宽如横断山岳,肌肉虬结如古藤盘绕,每一寸线条都...
水面之,暗流涌动,仿佛有万条细的生命声撕咬、吞噬、重生。
这是苗疆毒的蛊池,每滴水都浸透了年巫蛊的血,每缕纹都蛰伏着足以令原武林闻风丧胆的毒物——蚕蛊、噬蛛、七步断魂蛇,这些界被奉为圣物的凶虫,此处过是潭底寻常的囚徒。
而它们之,囚着道。
他的身躯几乎像凡所能拥有——肩宽如横断山岳,肌虬结如古藤盘绕,每寸条都像是被亲雕琢,完得近乎亵渎。
他的面容俊得近乎妖异,眉如刀削,鼻若悬胆,薄唇抿,便透出股近乎傲慢的冷意。
可摄的,是他的眼睛。
那眸子,原本紧闭,此刻却猛然睁——淡紫的瞳孔如两簇幽火,昏暗的潭底骤然亮起,仿佛能刺透尺寒水,首逼苍穹。
他抬头,望向水面之,嘴角缓缓扯出抹轻蔑的笑。
“武则……”他的声音低沉,却带着种近乎兽的嘶哑,仿佛喉咙还残留着被囚年的血腥气。
“你死我。”
水面之,来回音。
那声音严、冰冷,却又带着丝近乎病态的执着,像是銮殿的帝俯她的囚徒。
“朕你。”
“更让你受伤。”
“朕是要让你——乖乖为我所用。”
潭底的男笑了,笑声带着毫掩饰的讥讽。
“别梦了。”
“想要让我为你这肮脏的贱所用?
武则,你太搞笑了。”
他的声音潭水回荡,像是某种远古凶兽的低吼,连水底的蛊虫都为之战栗。
潭水依旧幽暗,蛊虫暗处窸窣爬行,像是数细的鬼啃噬着寂静。
那囚于潭底的男子——他的肌依旧如铁铸,紫眸依旧如冷焰,只是嘴角的讥讽更深了。
“朕很期待,未来你跪倒朕的裙。”
武则的声音从方落,带着近乎戏谑的傲慢,却又藏着丝难以察觉的执念。
话音未落,只赤红的噬蛊猛然扑向男子,獠牙森然,却触及他皮肤的刹那,被他声低吼震得魂飞魄散,仓逃窜,钻入潭底淤泥,再敢露头。
男子冷笑,紫眸眯,像是早己习惯这种谓的试探。
“虫子终究是虫子。”
——半月之后,武则如约而至。
她站潭边,服曳地,冠映,可那凤眸燃烧的,却并非粹的帝王严,而是种近乎偏执的征服欲。
她俯着潭底,唇角扬,像是早己准备新轮的唇枪舌战。
“朕又来了。”
“怎么?
骂过瘾?”
男子懒洋洋地回应,声音带着毫掩饰的嘲弄。
二唇舌交锋,字字如刀,句句见血。
武则身边的男宠们低眉顺眼地站着,气敢出,可却早己江倒——他们明,为何堂堂帝,竟与个囚徒对骂?
更明,为何每次,似的武,却总像是被对方压了头?
——两年后。
深宫之,烛火摇曳,龙榻的武则面容苍,眼却锐如刀。
她缓缓抬,指尖轻轻划,殿八的男宠便声倒,喉间血如丝,连惨都来及发出。
剩余的跪伏地,冷汗浸透衣衫,其尤以章郎、章郎得甚——他们的恐惧并非源于眼前的戮,而是源于……他们根本知道,己侍奉的“武则”,早己是正的帝。
他们知道,那个每半月去断魂潭挑衅的,才是正的武。
他们更知道,深宫的“苍帝”,过是具雕琢的傀儡。
——“什么?”
榻的“武则”缓缓,声音沙哑,却带着容置疑的压。
章郎牙齿打颤,额头抵地,颤声道:“奴、奴才是……是敬畏陛……武则”笑了,笑容森冷。
“敬畏?”
“你们连朕是谁……都知道。”
甲卫的脚步声殿回荡,铁靴踏过青砖,发出沉闷的敲击声,像是丧钟暗处悄然叩响。
他膝跪地,呈本玄折子,封皮以绣着龙纹,却烛火泛着诡异的暗红,仿佛浸透了血。
武则——或者说,此刻端坐于龙榻的“她”——伸出苍修长的指,轻轻折页。
纸页沙沙作响,死寂的殿显得格刺耳。
她的目光字句间游走,唇角渐渐勾起抹冷笑。
“谋权篡位……是有意思。”
跪伏地的李央猛然颤,额头死死抵着冰冷的地砖,冷汗顺着鬓角滑落,砸地,竟像是泪。
——他太清楚这句话的量了。
当年宗李治肯权,她便让李治“病逝”,再以秘术将他的尸身炼傀儡,端坐朝堂,言行举止与生异。
满朝文武察觉,那些忠耿耿的臣们,还对着那具行尸走呼“陛圣明”,殊知,他们的君王早己是具木偶。
而那些稍有异的臣,更是悄声息地“暴毙”,二却又能如常朝,只是眼呆滞,脖颈多了道细如发丝的红痕……李央作为男宠之首,曾亲眼见过她如何“处置”听话的。
——活剥皮,填入蛊虫,再以秘法控,让“他们”继续行走于间,连至亲之都出破绽。
“李央。”
方来的声音让他浑身颤,几乎瘫软。
“你作为朕的后,对朕隐瞒的很多啊。”
——后?!
章郎和章郎猛地抬头,瞳孔骤缩,可置信地向李央。
他们这才发,这位低眉顺眼的男宠之首,此刻虽如筛糠,可那身锦袍的骨架,明比寻常男子更纤细……李央——,或许该称她为“李央”——死死咬住唇,齿间己渗出血丝。
她早该想到的。
武怎么可能的信个男宠?
所谓的“男宠之首”,过是她另重身份的掩护。
“罢了。”
龙榻的“武则”忽然意兴阑珊地挥了挥,折子她掌风燃,化作缕青烟消散。
“朕没间陪你们玩游戏。”
她站起身,服曳地,笼罩着方。
“明起,把朕的痕迹部抹去。”
“只有面那位武。”
她的目光扫过众,后落李央身,轻笑声。
“尔等……记住了?”
殿死寂。
片刻后,重重叩首,额头撞击地面的声音整齐如。
“谨遵……陛旨意。”
——当,深宫某处暗阁。
甲卫膝跪地,低声道:“陛,断魂潭那边……”,正的武则执笔批阅奏折,闻言笔锋顿,朱砂纸洇,如血。
“他今……骂朕什么了?”
甲卫沉默瞬,才道:“他说……您迟早求着他出来。”
武则笑了。
“啊。”
“那朕……便等着他能嘴硬到几。”
章郎和章郎吊胆地过了很长段。
他们每武面前恭敬侍奉,眼却总忍住往殿暗处瞟,生怕某个瞬间,那位正的帝从缓步走出,用那冰冷的掐住他们的喉咙。
但子过去,武像是彻底消失了,连半点风声都没再出。
两兄弟渐渐松来,甚至偶尔敢武面前露出几谄笑意——尽管他们己也明,为何要对个傀儡如此讨。
“,你说……陛到底想要什么?”
某,章郎借着酒劲,终于问出了这个压底许的问题。
章郎捏着酒杯的指发颤,酒液晃荡,映出他苍的脸。
“谁知道呢……”他低声道,“或许……她只是等个机。”
——首到袁罡辞官的消息来,兄弟俩才猛然惊醒。
那,武朝堂发雷霆,摔碎了盏,怒斥师“识抬举”。
可章郎明见,她眼底闪过丝诡异的笑意。
“戏己场……” 章郎喃喃道。
“师入瓮……” 章郎接,嗓音干涩。
两对眼,皆从对方眼到了恐惧。
——前唐血脉,该彻底清洗了。
---山巅·后餐风声呼啸,。
袁罡和李淳风对坐于悬崖边的石桌前,壶浊酒,两碟菜,简朴得像两位当奇的告别宴。
“没牙就别硬撑了。”
袁罡嗤笑声,夹起块炖得烂的,推到李淳风面前,“嚼动就咽泥,反正你也没几活了。”
李淳风呵呵笑,布满皱纹的颤巍巍捧起碗,将碾碎,混着酒水囫囵吞。
——他算到了太多该算的事。
比如武每半月去见的那个紫眸男,比如深宫那些“暴毙”却仍能行走的臣,再比如……袁罡命注定的场劫。
“袁啊……”李淳风忽然抬头,浑浊的眼闪过丝清明,“若是将来有个子为你赴死……你可记得她?”
袁罡挑眉:“怎么?
你终于要给我说媒了?”
李淳风摇头,笑得意味深长:“我只是觉得……你这,活得太硬,该软些。”
——他知道袁罡懂。
所以后,当袁罡推李淳风的草庐,只到桌摆着的坛骨灰,和封字迹歪扭的信。
“友:风水你比我懂,这坛灰,随便埋个地方。
个……就安阁吧。
反正,你迟早去的。”
袁罡盯着信纸,忽然觉得山风格冷。
——安阁,那是武则年轻爱去的别院。